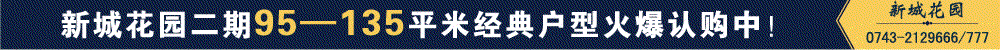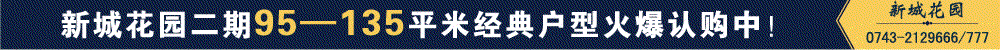文/杨智才 杨 睿 田艳芳辍学了。 作为班主任,我非得去看看她不可。 深冬,刺骨的寒风呜呜作响。我吃过晚饭裹着厚厚的棉衣,费力地蹬着自行车,暗暗地抱怨,这样的家长也真不明事理,为了挣钱,宁肯让心爱的孩子丢下书本。 不知不觉来到田艳芳居住的村口。 眼前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哪栋房子是田艳芳的家呢?我想打听打听,可又不见一个人影,小山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悲鸣。一个个门窗里飘出来的是歌声,喝酒划拳声,还有麻将的碰撞声。我面对那一个个整洁的小院不敢贸然而入,只得四下逡巡。一栋目前乡村很少见的、低矮的干打垒土墙房,犹如鹤群中的一只小乌鸦,在鳞次栉比的白墙红瓦楼群中,显得那么寒碜。 “这是不是田艳芳的家?”我心头颤动,“也许她真是因为家里贫困才辍学的呢?” 那小屋的门开着,我站在门口正想问,小屋内传出来一个亲切的声音:“小伙子,你找谁?”随着说话的声音走出一个人来,花白的头发上沾着一些碎草,深深的皱纹是他历经沧桑的标记,但他的眼睛却显得那么深邃,致使我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不知道应该称呼他大哥还是大伯。 我介绍了自己。“小伙子,是老师啊,不嫌脏就在屋里坐坐吧,外面好冷!”他给我让进了屋,找来凳子,用自己的衣袖在凳面上擦了擦,又用嘴狠狠吹了吹。他憨厚地笑着,那热情里含着诚意。 “您知道田艳芳的家吗?”我问。 “田艳芳?”他一愣,后又大笑起来,“不是,不是,她家住的哪能是这样的房子啊!她家住在前面,等会我带你去。先到我家喝杯水吧。”说完,他有把我引到里屋。 我慢慢地跟着他来到里屋,地面上堆放着很多竹篮子,有的是成品,有的是半成品。我心里想,一双粗糙的手,怎么能做出这样的细活来。室内很暗,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看清靠墙是两张普通的木板床,窗口那儿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些书。我仔细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 “小伙子,值钱的东西在这儿呢!”又是一阵开心地笑。我疑惑地望去,剥落的泥墙壁上贴满了大小不等、新旧不一的奖状。“这些奖状都是我的三个孩子上学得的。”他的话语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他接着说:“我也想盖房子、买电器,我还知道三个孩子不上学可以帮我干好多活,挣好多钱。可是我不能顾眼前利益,没有文化将来还是要吃亏受穷。” “我没有上过学,那时候我想干农活要什么文化,‘只有鼎罐煮米饭,没有鼎罐煮文章’,谁知道啊,我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要说我下的工夫比别人大得多,锄草、施肥、除虫害,没日没夜地干。到头来,收的粮食并不比别人的多。可没有文化,进城打工,工厂进不去,技术活干不了,只能下苦力,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没有本事找钱。那些高中生、技校生年纪轻轻的,既会种庄稼,又懂科学,养木耳、种草莓什么的,都发大财了,啧啧,我这个大老粗,也只有的眼红的份。” “你怎么不去干呢?”我忍不住问。 “人家是照着书学呀!唉,咱没有文化怎么干呢?”他停下手中的活,怔怔望着墙壁上的奖状出神。 我恍然大悟:“我懂了,你是把钱都投入到孩子读书上了,你要让他们好好读书,多学点文化科学知识。” 他竟像孩子一般咧嘴笑了:“别看我住的、吃的、穿的不如别人,这方面我可比他们强。我的孩子个个都很争气,老大和老二都考上了重点大学。老三正在上高中,成绩在全年级前几名……”他伸出大拇指,“老三比他两个哥哥还强!明年可能又是一个名牌大学生。万一考不起,回家还可以搞科学种田。”他把“科学”两个字说的特别重。 一股敬重之情涌上心头,我不由得再次仔细地打量着他,一件洗得褪色打了补丁的破棉袄,几处裂了缝的露出脚趾的解放鞋,乱蓬蓬的白发,刀刻般的皱纹,骨节粗大长满茧子的手,蕴含着独到见解的眼睛。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你找田艳芳有什么事吗?” “她不上学了。” “呀,那得去,小伙子,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田艳芳去上学,这个时代不上学可不行!” 告别了这座小屋,大伯带着我向田艳芳家走去。 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