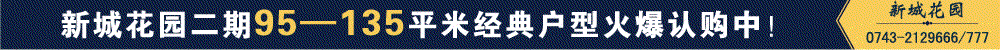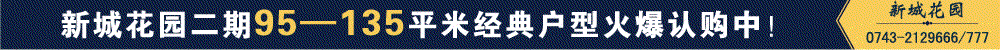熊 幽 武陵山脉趁着云贵高原的架势,一路惊峰,杵天杵地,朝东北方向奔赴。其中一脉,在湘西州州府吉首之南八公里处急急止步,撩下一块舒坦坪地和大小两根水脉来。 古人说这块土有乾象,取其名“乾州”。 在历史深处,乾州成了蜿蜒于武陵山腹地三百多里苗疆边墙下的堡垒之一。古堡镇守楚黔咽喉几百年,民谣颂之:“青岩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码口搭接线缝好,千秋永固乾州城。” “雄雷奔砦落,破月碍碉过。林户多依笔,儿童半负戈”的情状早成过去,如今,古城成了寻常的古城。古旧的老屋错错落落横排竖排,古老的窗台,黑黑的瓦脊,屋檐上长满金鸡尾草和岩衣草。房屋剪切出的弄弄巷巷作为曾经的战争工事,牛肠子一样在屋舍间序中有乱、乱中有序地打着活结或死套。在此上演过的无数瓮中捉鳖和关门打狗的故事已成为传说。 常有远道而来的男女老幼游弋其中,感受其千年郁结的味道。 “小小儿树,小小儿叶,小小儿树上落大雪……”童谣往往伴着薄雪,将古城的味道调和得粘粘儿的。 这味道,是从古城人的腔口儿发出来的。 关于乾州古城人的腔口儿,研究语言的中外专家和学者帮其划归湘语,也有认为是西南官话。结论是,因为土家苗汉杂居,语言相互影响,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平声读不送浊音,语感上比较接近西南官话;词汇语法看,它有着丰富的儿化音和重叠词。 这是沉淀于古城千百年的古雅的底味。 透过薄雪,古城飘出浓郁的梅花、兰花的清香。于是,游人的耳朵、眼睛、鼻子一个激灵,惊动了小小院落黄黄的腊梅、粉粉的红梅、素素的兰花,晕染出一幅美丽图画。足伫了,人的心却翻过矮墙黏住那画幅轻轻漾荡…… 先是一个小院落,一幅锦缎似的画图,接着渐进“牛肠子”深处,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虚掩着木门的小院,一幅又一幅或淡或浓经薄雪过滤的画卷。主人从画里走来了,年纪偏大,颜色偏暗,古宅偷袭了他们的年轮,花儿吸去了他们的颜色,古城赋予了他们纯朴与古雅。主客言语和手势并用,主题是古堡的逸事,当然还有从这里走出的正续写着乾州新故事的华韶人儿。 一时兴起,客人被主人邀进院子里。主人先是捧出乾州老红橘,这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品种红橘,曾经朝廷的贡品,橘皮薄薄儿的,红红儿的。客人接过两颗,喉咙暗暗滑动,轻轻一剝,红嘟嘟的橘瓣进嘴,轻轻吧唧一下两下,嘴巴就弯成了上玄月,眼睛就弯成了下玄月。那个香甜哦,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哦———哦———这个甜得很嘞!嗯,好甜,好甜!” 夸奖化作红晕染在主人脸上了,他又乐滋滋地端来醋萝卜。一定要尝尝乾州这特产的味道,你才能更加了解这座古堡的味道。客人用牙签戳了一片蘸了红辣椒粉的醋萝卜往嘴里送,“嘎嘣嘎嘣”几下,什么味道呢?乾州的醋萝卜是用米汤做的酸水娘泡的,萝卜是普通的萝卜,关键是看泡的时间掌握得好不好,时间不长短,泡出的萝卜色才鲜、味才浓、又香又脆。这打成粉之前拌料辣椒也有一定讲究,要色亮、不大不小、肉质不厚不薄,最好是邻近的泸溪兴隆场乡间的干红辣椒。切碎辣椒,小火翻炒后,趁热用石擂钵擂成粉,适当加些五香粉、食盐,再以翻滚的山茶油淋拌。哦,出味了!客人的嘴巴连续发出“嘘”声,嘴唇已红彤彤的了,耳朵也红彤彤的,红彤彤的鼻尖冒出了密密细细的汗珠子,忍不住喊了:“啊!乾州的味道!” 乾州的味道,是世世代代的乾州人用血汗和智慧酿就的陈酿。 几千年前,离乾州天远地远的北方大地,有两个部落因为争地盘打架,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架打得异常惨烈,被打败的部落首领蚩尤被杀。七零八落的部属败退南方后又历经不同朝代的打压欺凌,复而西迁。其中的一支将莽莽武陵山作为休养生息的隐身处,毅然决然带领子民进行第七次大迁徙。他们从沅水边逆武水而上穿越深山老林,战胜豺狼虎豹和毒气雾障,途径乾州大峡谷时留下一部分,然后往更深的腹地吕洞山地进发。留下的人种应是乾州最原始的住民之一,他们在万溶江边垦田种稻,下河捉鱼捞虾。 人类的历史由战争堆砌。之后陆续有人因为战争而躲进武陵山地。他们口音不同口味不同习性不同,但避难是共同的目的。他们各自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本领,在万溶江码头下船,先是战战兢兢打量着陌生的口岸,然后安身定神。傍万溶江边开了染坊、豆腐坊、榨油坊、碾坊……本钱小的摆摊设点卖小吃货,各自家乡的手艺和小吃在这里得以展示:醋萝卜、油炸粑粑、蒿子粑粑,凉粉、米豆腐、春卷、碗儿糕、糯米甜酒等等。慢慢,成集了,变市了。再后来,战火烧了进来。强的一方就用坚硬的岩石将已成街市的乾州围了起来,又用石灰糯米粉拌鸡蛋清刮缝,硬得铜墙铁壁一样,屯兵屯粮,练兵练枪。平时,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紧紧关着,出城进城得按着时辰。任敌方在外面怎么攻打,城里的该开店的开店,摆摊的摆摊,该读书的读书,该赏花的赏花,该玩鸟的玩鸟,熊克武带领的川军攻了二十多天没攻下乾州,至今古城人还津津乐道。 古城人祖祖辈辈曾经离战争很近,居安思危在代代人的骨髓里接力。人们建房起屋一律是筒子楼,没留阳台,窗户也小。挨街的则修成前店后居住、加工的窨子屋,柜台则有半人高,一律小门小窗。乾州人不现富,一天只吃早晚两餐,粗茶淡饭;衣着质地不大讲究,相信俗语“笑脏不笑烂”,烂衣服补得妥妥帖帖,洗得干干净净。依仗着冰冷的城墙,踩着坚实的石板街,日子过得充实而安闲。时不时出城,到溪谷坡面挖些兰草梅树,栽于庭院,套只画眉鸟挂于屋檐。庭院便灵动起来,得闲再一本一本读闲书,一笔一笔练字作画。花草是越长越旺了,一枝素心兰卖了天价。读书人是越来越多了,旧时有人从这读到了黄埔军校、北大、日本,有当了国防部长的、当了将军的,驱法护台的民族英雄杨岳斌,殉国于天津大沽口炮台的民族英雄罗荣光等,名声大得如雷贯耳。新时代,有从这里读到了硕士博士的。画家和字画是越来越出名了,跟着字画出名的有水冲石砚。水冲石砚虽晚于全国四大名砚,但因名士喜爱而享誉海内外。乾州名士杨味蔬所刻石砚,参加民国时代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还获得了金奖。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被召集到城墙根下,喊口号,表决心。城墙在“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被掀掉了。开始大多数人不习惯,后来想开了。和平年代,掀掉就掀掉吧。不要按时辰出门了,随便循着哪根“牛肠子”都可走出古城。似乎思想亮堂了些,胆子变得大了些,膀子甩得开了些。五花八门的手艺在外面的市场刷得很开堂,素心兰、爆炎肉、腊肉、乾州板鸭卖爆网络,蒿子粑、糯米甜酒、乾州红橘也是供不应求。连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醋萝卜,一年也能挣回来近千万票子。 新一代乾州古城人,凭智慧和勤恳正酿着古城新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