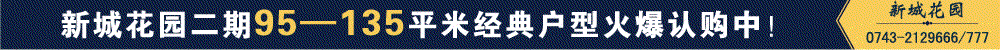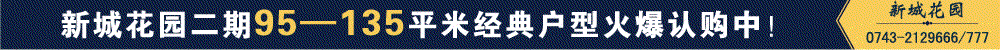麻垣杰 摄 文/陈雄 “回家的路有多长,离家就有多远。”这句名家之言,令我深思。可不管有多长,有多远,我们一直将走在回家的路上。 儿时,我以为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八面山脚下的历史文化古城里耶。 三天一场,五天一市,每逢赶集日,当站在村头“哨所”的公鸡第一声打鸣响起后,村里的叔伯婶娘们都会准时背着自家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满脸洋溢着笑容,途径村口的岩壁。当欢笑声在村口的岩壁上回旋几转后,八面山顶的这个小村庄又恢复了昨夜的宁静,唯有村头的那只公鸡仍在恪尽职守地“打更”。 村口的岩壁,光滑油亮,十几个年不及十的小孩子在夕阳殷虹的余晖下,穿梭在岩壁的凹凸缝隙之间。 “回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都将头瞥向村外。 若是叫如今的你看见,你定会惊叹这整齐划一的动作。兴许你还会怀疑,那一声“回来了”是“教官”的口令吧。 其实,里耶并不远,距家只有三十几里的路。十几年前,我第一次乘车去里耶,全程共花了5个小时。当时的车是农村古老的手扶式拖拉机,司机手握着摇晃的手柄,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坐在车上,不知疲倦地享受着这一路上带来的无尽刺激。车轮与山路撞击的余波淹及车上的男女老少,时而将你向左推去,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又将你拉向右,好不容易站稳了脚,又将你向空中抛得老高,好像在跟你开玩笑似的,准把人气得直乐。 初中以后,就独自一人在外,回家的路似乎又被拉得更长了。 最初离开家乡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尚不被更多的人知晓的小山,当地的父老乡亲仍旧过着早出晚归、面朝黄土,背朝天刀耕火种般的原始生活。 2002年,在里耶修筑河堤的时候意外地挖掘出了两千余年前的秦简,让这坐落在酉水之滨的恬静小镇闻名遐迩。八面山也因此得福,游客们欣然往之。可不管怎么改变,家乡在我心中的位置却始终如一。在那,有我的童年,我的憧憬,还有我人生中最珍贵的情谊。它是我心灵的港湾,是我一辈子魂牵梦萦之所。 每次回家,总是乘坐县际班车,每次路途上要倒两次车,花上一天的时间。汽车在山道上飞驰,望着车窗外飘飞的云彩,却想着家乡等着我的人和事。当然,也不全是云彩,有时蝶舞翩翩,莺歌燕舞,有时雷冰闪电,狂风下雪,在这几百公里的路途上,伴随着汽车的轰鸣,走过了一年又年不同季节的原野。 后来有一次,转车回到里耶,正值中午时分,却没了回家的车,奈何思家心切,于是决定重拾父辈的足迹,走山路回家。 继续背着几本精心挑选的书籍和衣物,不算重可也不轻,跟着一群乡亲,踏上了重温经典之行。天公也作美,太阳惬意而又慵懒地躺在蓝白相间的天幕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清风从悄然而至至轻然而去,带走了一行爬山者脸上的汗珠。 抬起头看看山顶究竟还有多远,可望见的依旧是山,似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爬到顶的山。渐渐地,体力开始有些不支了,双腿开始不容使唤地“筛糠”,肚子也跟着应和起来,似乎在催促。可再抬起一脚,似要耗尽所有的气力。 索然,转过身找一块平坦的石块,席地而坐,望着快要被山尖遮住的夕阳。 夕阳的余晖映红了眼前的山脉,那娇羞的红,分明就是村头岩壁上看到的红。恍惚间,回到了幼时,站在村头的岩壁上,看着父辈们洋溢着笑脸,背着从集市上换回来的生活所需之物,从容地走过岩壁,是回家,让他们显得越发从容。 当夜空群星闪烁,我踏着布满星辉的小路,回到了家。 回家的路,将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