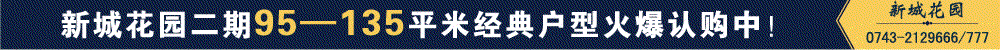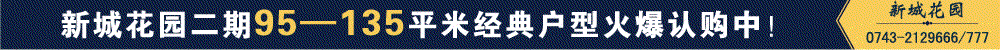九妹 这一场雨,旬月不断。 风雨湖里,从莲叶何田田到灼灼荷花瑞,雨气空而迷幻,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潮湿了一个季节。我也在小院植荷,清明时从乡下寻来一方老石槽,遂移植了去年赶集时买的红荷和白莲。还有虎耳草、兰草。还有一株盆栽白梅。莳花弄草,渐渐懂得雨水是最适合植物生长的,也就经常在小院摆放几个坛坛罐罐接雨水,檐牙如许,雨花时堕,满载着深深的板石巷弄的梦。 雨天夜读,文中写及《清嘉录》时有“梅水”一条:“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恍惚间,这一场无休无止的梅雨倏地清致迷人。透过二楼玻璃窗,一株白莹欲滴的栀子花,半掩着对面紧挨的屋檐,片片黑瓦,洗过似的光亮。院落里的一株芭蕉下,浸雨阶缝生出青苔,湿滑地上置着大肚水缸,漂着些枯败的植物茎叶,蕉叶滑落的、檐花滴落的雨水,在缸里乐此不疲的争相破开水纹…… 梅雨烹茶,是一壶梅花点茶。 这是我做的一款花茶。梅雨之前,春寒料峭,梅花一树一树绽放,数尽万般花,不比梅花韵,爱梅人就填了一阙《点绛唇》:“片玉纷来,寻幽心事今番了。微波渐杳,堤畔冰痕皎。丝柳风轻,破蕊梅花小。湘江绕,山中含笑,可似去年好?” 在这阵浮动的暗香里,可以绝望地思念某个人。我突然想到学古人自制“梅花点茶”:梅将开时,摘半开之花,带蒂置于瓶,每重一两,用炒盐一两洒之,勿用手触,必以厚纸数重密封置阴处,次年取时,先置蜜于盏,然后取茶二三朵,沸水泡之,花头自开而香美。———我摘的都是白梅花苞,摘一塑料袋装一大盘子,按一两炒盐一两梅花装瓶,却只装满一个拳头大的瓶子。 梅雨淅淅沥沥,时落时停,时停时落。当塑料瓶的梅花缩至大半瓶时,我就取一壶澄清两日的梅水烹茶,没有置蜜于盏,而是先沏了一壶雪片单枞,茶汤清莹透亮,取梅花三五朵泡之,骨朵儿像心事束缚已久瞬间便幽幽绽放开来,雪落如梅,梅开似雪,香气依旧是细嫩的。 花事如人事,清淡里隐约剪不断的宿契,就像两个清净如水的人,现世里一场相遇。 那天,是6月18日,我也取梅水泡梅花点茶,手机刷屏时看到网络消息报道102岁的张充和先生在美国去世,吃惊而沉痛,有些不能接受。张老的经世阅历就是一部生动的民国文学史和生活史,她的学识才华就是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写照和缩影。她的离世,让人在悲痛之外还有种深长的文化惆怅感。稍感安慰的是,得知她是在平静的安睡中离开的。 我是在迷上沈从文的时候,就迷上了张充和。我15岁时想学美术而去了凤凰读书,在渐渐熟悉沈从文作品的时候,也渐渐熟悉以诗书画昆曲“四绝”的张充和,每次去凤凰听涛山都会情不自禁地摩挲五彩石上张充和的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句尾四字“从文让人”,不仅透射出沈先生一生的高风亮德,也使人感觉到张家这个四妹是懂沈二哥的,真正地懂得。 几年前,我偶然在书肆翻到一本《古色今香》,为张充和题字选集,劲秀笔力、优雅书法,其中有她题签的《沈从文全集》,让我想起那一套二十多册的全集,书大盈掌,素雅封面,唯有书名题签的那一行楷书,像一朵朵梅花,清逸、秀洁。原来,1988年沈从文去世后,不少出版社都重印了他的旧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或者是纪念沈从文的文集,大多由张充和题写书名。 后来,我才得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百岁张充和作品系列”除了《古色今香》,还有《曲人鸿爪》、《天涯晚笛》。特意跑了几家书店,把两本书连同《张充和诗书画集》一起买了回来。捧书而读的时候,眼前仿佛就有一位慈眉善目的百岁老人,聚精会神地绘画题签,柔情清婉地抚琴唱曲,神色迷离地讲述民国往事。 从书中得知,张充和有一方印章,是清代篆刻大家杨澥的作品,文曰“梅花似我”。她就常用这个闲章,画一枝清逸墨梅,闲闲地生活在幽雅的古情古意之中,在中国时可以如此,在美国也可以如此。在耶鲁那个院子里,张充和养猫养狗,种植牡丹、芍药,栽种瓜菜、葫芦,还在草坪边角种植了一片青竹和一片中山陵香椿,就是这样,她也有遗憾,因为她最爱的梅树移植到这地方却一直不开花。 花花草草在女人心里都是有灵魂的。张兆和是张充和的三姐,也就是沈从文的夫人,在沈从文去世后,她一边整理沈从文的遗稿,一边在阳台上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1992年5月10日,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一半骨灰葬在听涛山五彩石下,一半骨灰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陪伴沈从文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她积攒了四年的玫瑰花瓣,以致沱江水面漂起了一道长长的美丽花带。 仅隔一年,即1993年10月下旬,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又转山转水来到凤凰祭拜沈从文。那年,我还在凤凰读书,凤凰旅游远不如现在这么火热,古城古街古巷子清清静静的,一脚伸进去半天转不出来。听涛山更是环美幽丽,沱江通脉,清滢秀澈,岩泽气通,如珠走镜,似仙境也。张充和夫妇爬上半山腰伫立在五彩石前,轻唤一声“沈二哥”,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这是张充和夫妇唯一一次凤凰之行,激动之情难以忘怀,她一呵气填了五首词,《张充和诗书画集》就记载了第一首《题沈从文墓》:“凤凰好,山水乐无涯。文藻风流足千古,苗家人是一枝花。此处最宜家。”沈从文是凤凰县人,这里是他的家。但是,墓在这里,才是真正的用意———永远的家。 冥冥然中许是有一种机缘,长满虎耳草的听涛山,就从那年开始满山遍野种植了梅树,有白梅、腊梅,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入山口种植了一株红梅,逸逸斜生在路坎上,老树虬枝绽放的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 张充和去世后,友人纪念撰文赞其为中国传统文化遗存海外的一株梅花。她永远也不知道,我每天都会去的风雨湖畔有一所沈从文纪念馆,纪念馆前面有一大片梅林,花落时候如雨,真乃古色今香。 时已夏至,梅雨依旧在下,潮潮湿湿弥漫起一缕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