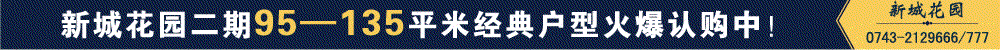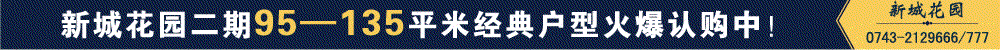张瑞田 画画的苏高宇写作,文章短小,语境泊淡。他的随笔集《恍惚》,收录了一百余篇文章,短则几十字、数百字,长则一两千字,平铺直叙,易读好懂。文章体例胎息传统的笔记体、书信体,说事就说事,谈人即谈人,不化妆,也不呐喊,一如禅者问思,或路人呓语。 读苏高宇的文章需要耐性,他不习惯繁冗地说教,也不去没话找话,显摆自己鹤立鸡群。短促的文字,克制着作家的情感,一笔笔,一字字,是一个人彼时独有的心绪、感想,是他一天的快乐与忧愁———读书、访友、画画、写字,或者是慵懒地遐思,天真地展望,不管有无意义,不管意义多大,这一天,这一个过程属于苏高宇。 我慢慢读《恍惚》,有恍惚的感觉。读书有两种目的,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散怀闻道,读苏高宇的文章,收获多半属于后者。其实,一个人的恍惚是从不恍惚开始的,也是从恍惚开始不恍惚的。这样的直觉有美学的道理,苏高宇形象而单纯地表现,让一种美产生了吸引力。“我常常醉心在水墨的情境里,是因为有了素的力量”,这是苏高宇在《素的力量》一文的开场白。然后他又说:“社稷、民生、部落,及至一个小的家庭,家庭里各个的心灵,总是向往着简单如素的。简单了就明澈;明澈了就安详;安详不就是平和,就是中庸,就是涵容广大?”素的道理,何尝不是做人、做文章、作画的道理呢。苏高宇对“明澈”、“安详”、“平和”的向往,在《冰心素面自可人》、《两枝浓郁的花》、《兰竹》、《空镜》、《八大如莲》等篇什中落地有声了。没有宏大叙述,没有高亢嘹亮,一如雨后的蜻蜓,在彩虹的光晕里漫无边际地飞行。有时,苏高宇是一只滑翔的蜻蜓,有时,苏高宇在一棵柳树下,用诗人的眼光,看蜻蜓飞来飞去。单薄的翅膀,被傍晚的霞光染得金丝金麟,也许,这便是苏高宇的恍惚。古人笔记,倾向于文献与经验。客观记录,史料钩沉,总觉得那些文字过于凝重。 苏高宇的文章,由现代汉语表述,语言开张,语意丰富,与书法、国画、篆刻紧密交集,与生命、生活相伴而行,独有的色彩,让我们喜悦,也让我们恍惚。作为作家的苏高宇画画,笔墨蓬勃,浑厚华滋。《恍惚》中收有一百余幅画作,有的表达山水之壮观,有的刻画梅兰竹菊之性情,有的寥寥数笔,有的纵横开阖。苏高宇的文章,与画有血缘关系。毋论那些富有弹性的题跋,还是独自的沉思;毋论是斑驳的书迹,还是浅色淡墨的低语,看画,就会想起他的文章,看文章,也惦记他的画。苏高宇真有本事,这一点,他的湘西老乡黄永玉做得出色,黄永厚不同凡响,还有半个湘西人的陈师曾与“二黄”也难分伯仲。我觉得,会写文章的画家应该仰视,画笔未尽的心意,语言能够弥补;语言不能直陈的愿望,笔墨会有另外的表达。 苏高宇的画是文人画。迩来谈文人画有误区,我们习惯性地把当代作家的画,或者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画视为文人画。总觉得简单,或者无法从简单中体味到丰富,也发现不了简单中存在的一个精神天地。其实,文人画的笔墨呈现有来路,它链接着旧日的时光,以及时间背后古人的一声叹息。是古人太笨了,还是我们过于世故?古人认定的路,会一直走下去,很难妥协。我们不行,风吹草动,我们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甚至倒退,重新选择。文人画有犟劲,它与画家的心紧密呼应,一叶兰,一杆竹,一块石,荔枝与石榴,荷花与松枝,是画家人格的外化,而那些短长的题跋,则是画家欲说未说,说了又说的心语。“此为老纸而不吃墨,辜负了岁月”,一幅淡梅,苏高宇写了这些字,显然是欲说未说。未说,其实也说了,“辜负了岁月”,人生况味几何,我感到了重量。《莫可名状图》有这样一段话:“枣糕蒸坏了就成了糟糕。糟糕是一块心情。”也是欲说未说的话。枣糕是形象,糟糕是心境,形象与心情相互牵连。文人画另一个要素是书法。苏高宇是作家、画家,也是书法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哀叹当下国画家书法的低劣。书法不精,题款便俗,遑论写大言长语了。苏高宇行,他的书法笔厚墨重、摇曳多姿,有唐宋气象。苏高宇的穷款犹如画龙点睛,长篇跋语,是画家深情的感喟,独自的思考。《四蟹图》中如此写道:“许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对于别人的环境与心境没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就产生了误会曲解。写过《浮生六记》的沈复说了,闷在蚊帐里吸烟,烟缕袅袅,见蚊虫隐显其中,便联想起云中的飞鹤。我们没有这样的境界,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有他作为尘世俗人的欲望与追求,行为方式不尽相同的时候,就尽量尝试着理解吧。”俨然是一篇文章了,写在一幅画的上端,俯瞰四只蟹的腾挪、对峙、搏斗,说了又说,没完没了。在当代国画家中,苏高宇的长跋有一定代表性。人生思考与文学思考熔铸书法、绘画之间,赋予一幅画作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黄永厚在写给戏剧理论家孙家琇的一封长信里,对当代国画的贫跋现象相当不满。画名与作者名,就是一幅画上的所有文字。因此,黄永厚说,当代很多的画家没有文化。他身体力行,他画画,他写文章,他在自己的画作上写幽默与思想性长跋。今天,他的同乡苏高宇见贤思齐,文、书、画,齐头并进,延续文人画的真正血脉。《恍惚》一书,便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