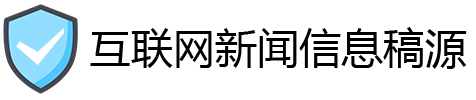邹群
从泸溪往南六十里,经浦市过达岚,至辰溪、泸溪、麻阳三县交界之地,层峦叠嶂处群山逶迤散开,一条静谧蜿蜒的溪水徐徐流淌,兰村获得了腾挪开阖的生存空间。
一
兰村人大多姓刘,传说上代太公为江西人,于江西填湖广时迁徙至于此,但见溪山回环,便于此处安家,随后又有包、邓两家迁移聚拢,不断营造居所,把生土变为熟土,把熟土变成农田。至今,村中的刘氏宗祠香火犹存,逢年过节,刘氏族人必集于祠内祭祀祖先。
兰村人家分五处:塘湾、屯里、板桥、碧溪、羊牯垴,地名皆取自地理环境。湘西乡下建房大多就地取材,若是山中多木头,自然是杉木建造的吊脚楼,若是采石方便的,则是石头房子居多,若是石头也没有,就以黄泥的土房为主。因此,兰村多为黄泥的土砖房,从田里取了泥土,泡水倒入砖模,成型晒干后即可砌房。
小暑过后开始入伏,是砌房的好季节。一家砌房,全村的人都来帮忙,男人们在田里将泥土在水中反复搅拌、夯紧,再将成型的泥坯取出,一排排摆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他们手上忙碌,嘴里还不忘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黝黑结实的膀子上全是黄色的泥巴,妇人们在厨房杀鸡剖鱼,煎炒之声,响连四壁,炊烟袅到庭前。房屋建成后再将谷壳、稻草混入泥中粉涮墙面,使其更为坚固、防潮。
这种黄色的房屋沿着山势铺展开,到溪边才停顿下来,户户庭前屋后都种桃树梨树,也有种柑橘的。春天时,桃红李白热热闹闹地挤满了院子,豆角花爬上篱笆,引来无数粉蝶翻飞;秋日里,一枝枝柑橘从土墙上垂下来,会碰到路人的额头上。
路边的土地祠,因陋就简,泥墙泥瓦,只供一尊须发皓然慈眉善目的石佛,香案上有陈年的蜡烛及点剩的香棒,两旁贴着“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在湘西乡下,土地祠大多居于树下或路旁,以两块石头为壁,一块为顶,有条件的塑个神像,否则竖个木头牌位也行。
兰村有溪,名曰太平溪,有佑一村太平之意。太平溪波微水缓,一路向东,连接至沅江,溪水清澈见底穿村而过,可浆洗、灌溉,傍晚时常有野鸭成群结伴停在水边清洗羽翅。溪上多有石桥或跳岩,水边长满芦荻,高过人去,春日里一岸翠绿,秋天枯黄了,一片片雪白的丝穗在风中起伏翻滚。水芋、黄菖蒲随流水缓缓摆动,野莺和水鸟停在岸边的石头上晒太阳,有人靠近时,便齐齐拍着翅膀从水面低低掠走。
我外祖母家住在屯里,门前是太平溪,溪对面有大片幽深茂密的竹林遮天蔽日,盛夏里进入林中,骨头都沁得冰凉。我后来读屈原的《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脑子里总会出现兰村的这片竹林。
兰村虽属泸溪县所辖,却因与麻阳县城相近,故村民皆讲一口的麻阳官话。比起生硬高亢的泸溪话,麻阳话则更为绵软,颇有吴侬软语的婉转。
二
十月小阳春,田稻都割尽了,此时办斋酬神是湘西的习俗。
较小的寨子舞蚌壳灯耍彩龙船,大一点的村子要搭台做戏文。明末江西弋阳曾氏兄弟弃官避难至此,常以哼唱弋阳腔来思念家乡,后人将本地的儒释道音乐、放排号子、民间歌谣融入其中,就形成了辰河高腔的雏形。也因此,兰村人熟通戏文擅唱高腔,有自己的高腔班子,虽三岁孩童亦知曲唱,便不觉奇怪了。
兰村搭台唱戏,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赶来看。种地的放下锄头,织布的停了机杼,经商的关了店铺,嫁在外地的女眷是用轿子去接了来,家家都有几桌客人。
戏台搭在祠堂外,台下摆满了摊贩,卖甘蔗、柑橘、凉薯、荸荠,还有热气腾腾的油条、灯盏糍、剩饭糕,热热闹闹一直摆到了田坎上去。只见人头攒动,推来推去像潮水,女眷们吃着瓜子相互攀谈,不时发出低低的笑声,男人一边大声地打着招呼,一边看她们,小孩子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流着鼻涕在摊贩前钻来钻去,刚吃完这个又吵着要买那个,这样沸沸扬扬直到鸣锣开戏。
高腔有锣鼓钲笛唢呐来配,长相清秀俊美的扮旦角,先来一出《放告认母》,然后是《洗马沐鞭》、《专诸刺僚》,一出紧接着一出,待到发五猖、捉寒林、打叉捉鬼时,演员跳下台,在观众中穿插打斗,大刀长剑于头上挥动,惊得众人连连唏嘘退让。到了最后“目莲戏”是高潮,台上钢叉翻飞,一口漆得乌黑的棺材就摆在戏台下,若是演出时失手出了人命,便随手塞进棺材里去,与他人无关。
唱到目莲在阴间十殿寻母时,佐以唢呐、笛子帮腔,一时如泣如诉催人泪下,一时又似万马奔腾地动山摇,众人紧挨着棺材,都屏住呼吸,心悬在嗓子眼里去了。汪曾祺曾经说过,川剧的帮腔运用“间离效果”,不要求观众完全“入戏”,要保持清醒,和剧情保持距离,而高腔中唢呐、笛子模仿人声帮腔,亦同此理。
看完四十八本连台戏已经是半个月后了,众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冬日里农闲,是乡下人嫁娶的好时节。板桥人家做亲,唢呐吹得五里外都能听见,嫁妆从路上抬过,雕花的镜匣,大红的丝绸被面,沿村的女子都出来看,叽叽喳喳直看得眼睛发热,暗自筹谋等到自己出嫁的时候,定然也要置办这么一套妆奁。只是,他几时来家里提亲,爹娘又会不会答应……花轿过处,留下了兰村女子如针脚般细细密密的心思,夜里听着太平溪水哗哗响个不停,久久无法入睡。
最小的姨娘大我十五岁,平日里最疼我,在家舂米背着我,出门看戏也背着我,没人的时候,我叫她姐。她十八岁那年,媒人上门提亲,男方是吕家坪开豆腐坊的向家老三,兰村人都说,姨娘嫁过去享福了,以后有吃不完的豆腐。
姨娘出嫁前三天,不吃不喝亦不梳洗,一个人坐在屋里断断续续地哭,我心里像是有一样东西塞得满满的,却又说不出来,便跟着哇哇大哭。姨娘听了,停下来问我:“崽妹,你哭哪样?”我哭着说:“我也不晓得。”姨娘拿手帕给我擦鼻涕:“崽妹,以后要听嘎婆话,我得空了转来看你们,买糖给你吃。”我紧紧抱着她不撒手:“姐,我不要吃糖,我只要你。”
到了正日子,新郎来迎亲,花轿到了门口,姨娘扑到外祖母怀里嘤嘤啜泣,只恨以后不能在爹妈跟前尽孝,又舍不得一起长大的姊妹,也骂媒人,骂吹鼓手。她一边哭,一边骂,直听得女眷们都眼睛发潮。将及卯时,吉时已近,舅舅背着姨娘上轿,于是,鼓乐大作,媒人点了火把在前面引路,一行人马浩荡,吹吹打打沿着太平溪往西去。屋内突然变得空荡冷清,外祖母便放声大哭,溪那边隐隐传来两面锣声:“白生——白养——”
三
过完年,溪水肥了,春天也就来了。
二月里,便有“春倌”提着篮子挨家挨户唱送《春牛图》,他口中唱些劝人为善勤俭农作之词,那篮子里装着木刻版印的《春牛图》和新黄历,上面写了来年的二十四节气预告。主人收下春牛图,将其恭恭敬敬地贴在大门上,再回给春倌一些零钱,或一碗米几个糍粑,然后春倌又去第二家。
接了《春牛图》,意味着育秧播种的时候也要到了,兰村人对育秧播种极讲究,要带了三炷香纸插在田塍上,拜完五谷神才播种子。对于他们来说,遵循着天气的变化和神明的指引生活,若是还有困惑,便去请教刘先生。
湘西乡野经常会有些颇为雅致的人物,这种人豁达洒脱,往往一肚子的学问,或写得一手好字,或画得一手好画,甚至对诗词楹联也是极擅长,这种人看似平平无奇,与你论起经史子集来,会让你觉得山河浩荡豁达明亮,外面的天下世界都到了堂前来。
住在外祖母家隔壁的刘恒良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刘先生自幼酷爱听戏,五岁能唱,声音清爽,吐字圆润,十五岁到县城读书,是村里难得学过新学的人。之后随浦市双少班四处演出,下过常德,去过黔阳,年近六旬才回到兰村,自此赋闲在家,整日里读书唱戏,或去太平溪垂钓。有村民带着子女上门学戏,刘先生也都耐心相授,不收分文。众人过意不去,逢年过节便让自家孩子给先生送去一筐山薯,或几尾鲤鱼。
外祖母见母亲每日趴在土墙上看刘先生教戏,便带着母亲上门,行了拜师礼正式学习高腔。后来,县里成立辰河高腔剧团要招学员,兰村自然成了首选地,十二岁的母亲因扮相秀美唱腔婉转,经刘先生推荐考入县剧团,从而改变了一生。
刘先生是在过完七十岁生日走的。在乡下,过了六旬算喜丧,所以后辈并无悲伤,孝子去太平溪取了水,给先生洗身更衣装殓。然后扎孝堂、罗孝帷、点长明灯,由族中长辈编派,大家各司其职。
深夜里,大家围在先生的棺前听歌郎唱老人歌。开始是一个人在唱,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多,像是有很多人在附和着一起唱,那曲调没有太多起伏,如同一条平静的河流缓缓流过,无始无终。长途迁徙的苦难,劳作生息的艰辛,以及人生短促、老之将至的悲叹,这歌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四
立冬,我陪母亲回到兰村。
自外祖母过世后,母亲再没回过兰村。一路上,山谷两旁的各色植被一层层往上铺开,河床边的小树密密挤挤地长在一起,八十二岁的母亲如孩童般快乐,见山也亲遇水亦喜,路上看到成群的山羊和鸭子,也要絮絮叨叨跟我讲上半天。
中午抵达兰村,我们的车从村头开到村尾,又从村尾回到村头,最终停在溪边的文化广场上。下了车,母亲眯着眼四处张望,嘴里喃喃道,田埂呢,土墙呢,怎么都不见了……她努力将记忆深处的碎片拼接成家的模样,可是与二十多年前母亲最后一次回到兰村时相比,新修的乡村公路,路边停放的一辆辆小车,以及错落有致的栋栋别墅,早已不是她记忆中故乡的模样。
站在兰村,母亲却找不到家。
开河和老猛把我们接到家里。开河是大舅舅的儿子,老实憨厚不善言辞,老猛是二舅舅的儿子,狡黠中透出精明。八十年代初,为了寻找机遇,他们和村里其他年轻后生一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凭着踏实、肯干的性格和常年砌土砖房的手艺,他们很快找到了生存之道,于是拖家带口,从最初做砖做瓦卖苦力,到后来成立了建筑队、基建公司。
前几年,国家精准扶贫的好政策犹如一夜春风,吹活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们的心。回到久别的兰村,他们大刀阔斧地开垦山坡荒地,建了黄桃、冰糖橙等新型果木基地,又大量种植茶油、药材,通过互联网销到全国各地。还有人在村里办起了养殖场,散养些猪、牛,发展壮大后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让生猪养殖业走上了基地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生产道路。如今,兰村人家家养猪户户喂牛,种稻子的,改良了品种,种天然绿色无公害有机米卖到省城,收入颇丰。
“我种了五百亩油茶养了三百头猪,猪圈就建在油茶林里,猪粪发酵后转化成油茶林的肥料,节省了大量成本,效益更高。老猛比我脑壳活,他跟年轻人学网络直播,把村里的柑橘、芝麻和腌菜都卖到北京、上海去了。”说起现在的生活,开河咧开嘴笑了起来,脸上的褶子像朵绽放的南瓜花。
百年历程,山乡巨变。从渔猎到农耕,宽广的太平溪不仅赐予了兰村人财富,更造就了兰村人过人的见识和谋略。他们热情、乐观,守着一份家业,过平实安稳的日子,又能接纳新的思想,在机遇到来时大展拳脚。如今,族中子弟在外为官、求学者不少,更甚者,已是州、县教育行业的领头人。
午后,我们坐在老猛家的院子里闲话家常。
立冬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红色的蔷薇浓烈地铺满了院墙,老猛说,儿子已经在麻阳县城买房成家,女儿去北京上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工作。母亲听得连连点头,好,好,孩子们都出息了。随即又伤感道,他们走出大山,见了世面,只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看着门前从容流淌的太平溪,老猛笑着说,每年春节孩子们都会回来,不管走到哪里,兰村永远都是他们的家。
是呀,顺着水走,就是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