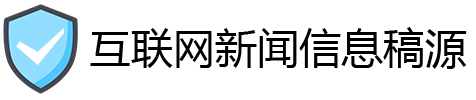朱小平
有年中秋回湘北娘家省亲,颤巍巍的老祖母仍把我当作寄宿在外的学子,执意往我已然胀鼓的回程行囊里,塞了一玻璃罐她亲手腌制的醡辣椒。
始龀之年的幼女蕤儿,盯着那罐透着胭脂红的细碎米粉,伸舌头舔了舔嘴唇,豁着门牙一脸稚气地问我:“这是不是散装的酸梅粉呀?”阅多识广的家婆接过玻璃罐,转着圈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也只辨出米粉里混着剁辣椒,猜测是道菜,却叫不出名字。想来,醡辣椒该是我家乡那一带独有的风味佐餐菜。
我当即做了一碗老少皆宜的醡辣椒浓汤。循着记忆里祖母的做法,先舀出生干红粉,用凉开水浸发至湿润,再倒进热油锅;一边用锅铲不停搅拌,一边慢慢加水,免得粘在锅底烧成黑锅巴。很快,我的视线就被沸腾的蒸汽笼住,分不清锅里此起彼伏的泡泡,是像雨滴坠入溅起的涟漪,还是像狡黠小泥鳅搅出的漩涡,只觉阵阵辣香往鼻尖钻。待一铲铲白里透红的米糊糊起锅,撒上鲜灵的绿葱花,家婆迫不及待夹了一筷,竟像孩子似的吮着筷头,啧啧称赞“软糯酸爽,真开胃”;蕤儿则一汤匙接一汤匙往米饭上淋,红糊糊拌着白米饭,辣得额头冒汗、酸得牙打颤,还直喊“好吃又好看”——那模样,和我儿时吃醡辣椒浓汤时一模一样。
其实在老家,醡辣椒最惯常的吃法是炸炒。菜籽油要多放些,大火炸到表面呈暖融融的阳光黄,再转中火翻炒均匀,最后调小火焐熟。炸炒好的醡辣椒不用加任何佐料,颜色金红油亮,嚼着焦脆筋道。那股重口味的咸辣,让人没法囫囵大口咽,只能一点一点慢吞慢嚼,成了日常里细水长流的下饭菜。偶尔我等不及全家人上桌,伸手就想拈着吃,祖母总会用桑皮色的草纸,轻巧包好一锥角熟醡辣椒,给我当垫肚子的“零嘴”。遇上有客人来,祖母做醡辣椒就会换花样,总要搭配些荤菜——熏腊肉薄片、酥骨小鲊鱼,或是去壳的鸡蛋。这样一来,积淀的盐味散开来,咸淡也刚刚好。“懂得融会贯通,你才算‘贤惠’(咸会)哟!”祖母说着,双层圆桌面已摆满热腾腾的菜,缓缓转了起来。
我忽然想起祖母家台阶上那台古旧的石磨。大小重叠的两块圆磨石,像静默流转的日月光盘,从容地碾过生活里的繁杂,把坚硬磨成柔软,把粗糙磨得细腻。祖母总围着磨石转:打豆浆、碾酒药丸、磨米粉,或是做糕点、腌醡辣椒。石磨上密匝匝的刻痕,渐渐延伸成她脸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勤劳的祖母不光自己闲不住,也看不惯我们晚辈故意偷懒。她干活时总爱扯着嗓子喊我搭手:“乖孙女来帮我添磨啦!”她那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头禅,也悄悄潜移默化成了对我的“养活教育”。
我伸出小手,把磨心裡粘糯的混合米粉掏干净,祖母还要再过一遍筛。过筛是个简单动作,用处却不简单。就像金沙过筛,漏掉沙土、留下金粒;祖母筛米粉,筛上的粗米粉用来拌剁椒腌醡辣椒,筛下的细米粉则做发糕、米饺——一点都不浪费。原来,筛选的意义,多半是由筛粉的人赋予的。
醡辣椒的灵魂,终究在剁辣椒上,而且必须选立秋后收的尖红椒。春夏季雨水多,早红辣椒看着艳,水分却太足,鲜吃味道好,腌起来却容易烂;晚熟的秋辣椒没了急功近利的劲儿,肉质紧实、辣味十足,剁了和米粉拌在一起入坛,多放些盐,腌好的醡辣椒就算放久了,滋味也不会变。真正的美食,从不怕费时间,也经得住寂寞的等待与守望。
那年暮秋,祖母的身影停在了一片刚摘完秋辣椒的地里。后来蕤儿总跟我提“祖母味的醡辣椒”,勾得我思绪翻涌,便写下了这些文字。不知不觉间,蕤儿也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