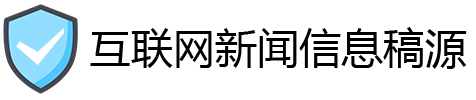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

寂静的老街。

抬眼是青山。
文/李诗好 图/石流
泸溪的清晨,是被沅水摇醒的。
雾还没有散尽,懒懒地浮在水面上,把对岸的橘颂塔也泡得软了轮廓。江面平得像一块青灰色的玻璃,只有早起打渔的小船,用橹尖儿划开一道口子,又轻轻合上。巷子深处传来“吱呀——”一声,不知是谁家的木门,推开了晨光。
那香味,就在这时飘了出来。
细细的,一缕一缕的,和着晨雾里的水汽,像是从江水里捞起来的气味。不浓,却韧得很,顺着石板路窄窄的缝,慢慢地爬,慢慢地染。等你察觉时,整个白沙已浸在这片温润润、潮乎乎的香气里了。
这就是斋粉的味道。泸溪人的一天,便从这个味儿开始。
本地人说,这是“最泸溪的味道”。不腻不荤,清清爽爽的,倒跟这沅水的气质合得很。
粉店的灶台总是最暖的。系着蓝布围裙的老板娘,手在热气里穿梭。抓一把雪白细长的米粉,在竹笊篱里轻轻一抖,落入海碗。舀汤是个讲究活儿——那汤熬了一夜,在粗陶罐里“咕嘟咕嘟”地唱着。汤色清亮,能照见人影,偏偏香味浓得化不开。是胡椒,又不全是胡椒,还有点说不清的温香,只觉得一股暖意顺着呼吸往心里钻。
粉端上来时,碗沿腾起白雾。先喝一口汤,那暖便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整个人都舒展开了。粉滑嫩得很,筷子要夹得轻巧,稍一用力就溜走了。轻轻一吸,“嗦”的一声,满嘴都是清甜的米香。
有意思的是这吃粉的人。
靠窗的老船工,吃得呼噜作响,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他说江上的湿气重,这碗粉下肚,一天都不冷。旁边的小学生踮脚趴在桌上,鼻尖沾了汤渍,眼睛却亮亮地望着——那儿,朝阳正爬上涉江楼的飞檐。最安静的是戴银饰的阿婆,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手腕上的银镯子偶尔碰着碗边,“叮”的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
这粉原是再简单不过的——不过是米和水。可就是这最简单的,反而最见功夫。米要本地高山的米,水须是沅江上游的水。做粉的人半夜就要起来,浸米、淘洗、磨浆、煮糍、榨粉、漂水……忙到天色泛白,头锅粉才算成。
都说湘西的山水养人,我看这碗粉也养人。养出了泸溪人不急不躁的性子——就像这沅水,淌了千年,还是这么不紧不慢地流着。
吃完粉,身上暖了,便想去江边走走。
雾散得差不多了。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把江水切成两半——一半是亮的,粼粼地闪着碎金;一半还在影子里,青沉沉的。辛女岩看得真切了,就那么静静地立着,像是看着江,又像是什么都没看。
老人沿着江边步道慢慢走,步子匀匀的。几个骑车少年掠过,带起一阵风,惊起了岸边的白鹭。江心有渔船,船头站着鹭鸶,黑色的,铁铸的一般,忽然一低头,便衔起一尾银光。
想起沈从文当年坐船过泸溪,说这里的清晨“总有烟火与诗意交织”。这烟火,大概就是粉店里冒出的热气;这诗意,或许就是此刻江面上跳动的光。
其实烟火与诗意,在这里原是一回事。
下午再经过粉店时,客人少些了。老板娘闲下来,坐在门口剥花生——那是明天要撒在粉上的。阳光映着她的侧脸,安详得很。巷口的香樟树下,几个老人在下棋,棋子落在木棋盘上,“啪,啪”慢悠悠地响。
这才是泸溪真正的好——不慌。日子在这里,像是被江水浸过似的,绵长而温润。
黄昏时,最后一碗粉总是卖得最快。归人也好,旅人也罢,带着一身的疲惫或风尘,坐下来,不说话,只是慢慢地吃。等一碗粉见了底,抬起头时,眼神都柔和了些。
夜色从江面浮起时,粉店的灯亮了。黄黄的光透过窗纸,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团暖意。远看,像江上的渔火,一点一点的,静静地亮着。
而斋粉的香味,早就融进了这座小城的骨血里——就像沅水千年如一日地流着,就像辛女岩永远那么站着。它们不说话,却什么都说了。
“爸,下次来襄阳,记得带米粉。”儿子的话音似又在耳边响起。
或许,所谓乡愁,不过就是某个清晨,突然想起的那一碗清汤,几缕米粉,和那口怎么也忘不掉的、暖暖的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