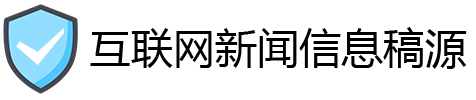创作同时,陈建平还从事书法篆刻培训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新秀。

陈建平的刻刀在方寸之间游走,以刀代笔,把篆法、章法和刀法融为一体。

“司马刀客”陈建平,人帅,字正,印雅,调低。

陈建平篆刻作品《游鱼出听》。

陈建平在工作室的黑板上张贴了一张苏东坡人生轨迹图,以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
文/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朱开朗 图/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张谨 团结报见习记者 胡承鼎 黄新媛
那天夜里,我和陈建平坐在他的工作室,喝着他泡的生普,聊起了陈年往事。
青少年时的陈建平,是尝过一些苦头的。
一
我和陈建平在2003年同时进入湘西美术学校读书。十六七岁的年纪,似乎懂了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懂。陈建平和我一样,从小热爱绘画,立志长大后要做个画家。每到上专业课或进入练习时,陈建平总能沉浸其中。
那时的陈建平,中等身材,头发微卷。眼睛不大,但目光很直;话不多,但嗓音浑厚。
练书法时,老师教导我们说为了保持执笔的手不抖动,最好每写一道笔画时,都憋住气。陈建平对自己要求特别高——他一口气要憋到整个字写完,然后再长舒一口气,接着又深呼吸,憋住气写下一个字,导致我们在上书法课时,总感觉教室里有一头牛在。打篮球时,他擅长背身靠打,像一头牛一样横冲直撞;学习时,他勤学苦练,像一头牛一样用功,加上他讲话声音浑厚如牛,久而久之,同学们都戏谑地称他为“牛”。
陈建平的刻苦给他带来了耀眼的成绩。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书、画、设计等专业课程均名列前茅。毕业前两年,学校给我们分班,分别是“艺术设计班”和“纯艺术班”。艺术设计班着重广告、装修、服装、装饰等商业美术课程,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出去找工作挣钱;而“纯艺术班”则是单纯地磨炼画技,培养方向是画家、书法家或美术老师。陈建平思虑良久,选择了“纯艺术班”。他说,他儿时的梦想、多年的夙愿,就是做一个画家。在班里,他依然是最刻苦、最好学、成绩最好的那一个。
但他在“纯艺术班”只读了一年,就申请转去“艺术设计班”了。对此,我常抱疑惑。问他,他沉默不语。
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得知,那时,他的父亲母亲为了供他读书,放弃了家里的田土,跑到吉首打零工。父亲还好,懂点手艺,常给人做一些木工活;而母亲只能在工地上给人煮饭、打扫卫生。陈建平之所以转入“艺术设计班”,就是想毕业后立马投入工作,然后挣钱。
学期结束,陈建平拿出了他最得意的水彩画作品——一张全开的《雪景图》,作为毕业作品交给了学校。该画着色厚重、手法灵动,构图巧妙,虽是水彩画,却也有着中国画的风骨,至今想来,那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不出意外的,陈建平以高分毕业。
二
2008年夏天,毕业前。一大帮同学相约着走了趟凤凰,去看沱江,去看古城,疯玩了很久,方才回到学校收拾行李。
那个炎热的下午,阳光格外刺目,照在身上有一股灼烧感。我和陈建平站在操场上,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着行囊离去,和他们嬉闹着告别。
一颗篮球静静地躺在球场上,陈建平低头看了良久,然后给我一个挑衅的眼神,问道:“单挑?”
我还以挑衅的眼神:“虚你?”
于是二人在众毕业生惊诧的眼神里,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你来我往地打起了篮球。按照惯例,先得10分者赢。我终究是不敌陈建平的拿手绝活背身单打,败下阵来。
“牛,你是真牛。”我丢下一句话,然后拖着疲惫而黏稠的身子去洗澡了。等我洗澡回来,同学们都走得差不多了,陈建平也不见了踪影。
“他说要赶车,先走了。”一位同学跟我说。
陈建平的父母就在吉首,陈建平的老家就在太平。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无需“赶车”的。若是赶车,他怕是去得比较远了,我想。
我没猜错,他去了重庆。
陈建平应聘了重庆秀山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他想要当一名广告设计师,靠着自己的专业水平,创作作品,构建自己的广告设计理念。然而理想总是被现实残酷地打破。刚出学校的陈建平,只能谋到广告制作和广告安装的职位。
广告公司的生活相比学校,更苦。
晚上,陈建平得守着喷绘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喷绘布从机器口里一寸一寸吐出来。吐到一尺左右时,陈建平就要上前把它卷起来,以免喷绘布皱在一起,影响效果。白天,陈建平就坐在老师傅的摩托后座,四处去安装广告。有时爬上房顶,有时爬上路旁的T形广告牌。在顶上站稳之后,再用绳子拉起数十斤重的喷绘布,拉伸、展平、固定。
“高速路边的T形广告牌,有的有几十米高,站在上面心里很虚,哪怕有一阵风吹过,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抓紧扶手。”时到如今,陈建平依然恐高。他的工作室在12楼,每次临窗,他都只敢远眺,不敢俯瞰。
一次公司制作一张巨幅广告,需要喷绘机喷绘一整夜。陈建平太累睡着了,导致喷绘布堆皱在一起,整夜的喷绘都白费了。陈建平被老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从那以后他上夜班再也不敢打瞌睡。
日子虽然又苦又累,但陈建平从没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宿舍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等待喷绘的时候,陈建平会拿一支毛笔,沾上水后在水泥地面练习书法。时间充足时,他会练习两个小时以上;时间再不济,他也会在睡前抽出十分钟写几笔。
“画画的话,需要选景、需要准备材料、还需要画板画架。而书法,一支笔就够了。”陈建平说,“那时我刚刚换了一个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每当我在水泥地上写出满意的字,就赶紧拍下来,不然过一会儿就干了。”
那时,我也离开了与书法美术有关的行当,我清楚,在走上了不相干的工作岗位后,还能长期坚持每天练字的,原因无他:一、执着;二、爱得深沉。
聊到这里时,我想起自己的不争气:一旦转行,就再也提不起画笔了。
就在我无言时,陈建平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似乎想要给我个台阶,他说:“那时刚刚结束了楷书临帖,练完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勤礼碑》,正在学习《张黑女碑》的起步阶段,一天不练都不行,会荒废。”
此话一出,我更尴尬了。回想起今年过年时勉强写的春联,不由想起老舍先生对他书法作品的自嘲:一串倭瓜。
“我吃不了苦,在重庆待了一年就回吉首了。”陈建平继续化解着我的尴尬,转移了话题。
此话一出,我再度陷入尴尬:我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若是让我去守喷绘机,或者爬广告牌,我怕是一天也待不住。
三
2009年,陈建平回到吉首,带着手机里那像素惨淡的照片,找到我们的书法老师黄峥嵘,请黄老师为其指点。黄峥嵘惊讶于陈建平的坚持不懈,也欣喜于陈建平的进步神速,更是爱惜陈建平“水泥地上临帖”的精神,遂对陈建平倾囊相授,陈建平的书法造诣愈发深厚。
那时,黄峥嵘已是湘西书法界大家,每天登门拜访的学习者络绎不绝。黄峥嵘看陈建平书法水平稳步上升,便对他说:“我这边事情也确实忙,今后再有人上门求教,就由你去指点他们吧。”
就这样,陈建平的名气越来越大。2011年,陈建平创建了自己的书法篆刻工作室,一边接收学员,一边研习书法和篆刻技艺。彼时的陈建平,已经完成了对魏碑《张黑女》和隶书《张迁碑》的研习,对书法线条的把握炉火纯青。他作出一个决定,跳过行书,直接学习草书。
在黄峥嵘的指点下,陈建平继续学习了孙过庭《书谱》、张旭《古诗四帖》以及怀素《自叙帖》。由于草书作品变化多端、大疏大密,常需印章来协调画面,陈建平在钻研草书的同时,对篆刻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
书法篆刻本同源。陈建平书法造诣深厚,加之刻苦努力,很快就在篆刻技艺上有了不少心得。一时间,不少书法爱好者登门拜访陈建平,求陈建平为其篆刻印章。
自2012年加入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后,陈建平便年年冲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选拔。陈建平的草书水平已经获得省内外不少大家的认可,但每次离中书协会员总是相差一步,久而久之,陈建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是从16岁才开始接触书法,但是全国范围内有很多人从四五岁就开始学习了,有‘童子功’的人都还有很多进不了中书协,何况我一个半路出家的。”那时的陈建平对进入中书协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与朋友聊天句句不离中书协,为中书协的事情茶不思饭不想。
篆刻家前辈肖五洋爱才,看出了陈建平的迷茫,他给陈建平出主意道:“每一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的入展作者都能备选中书协会员。你的书法作品如果行不通,何不试试篆刻呢?”
陈建平茅塞顿开,从此更为刻苦地学习钻研篆刻技艺。在肖五洋的引荐下,陈建平还认识了青年篆刻家文佐。陈建平常与文佐交流学习,篆刻技艺进一步精进。
2018年,全国书法篆刻展指定题材发布——参展者需篆刻一方“长风破浪会有时”字句的印章,组成条屏送选。陈建平如获至宝,连夜赶往长沙与文佐相会,商议参赛创作事宜。
经过反复探讨,陈建平决定以自己最为拿手的“战国古玺”风格来创作这方作品。他不断构思布局、尝试阴文阳文,刻了又改、改了又刻,终于在截稿前一个星期,确定了送选作品。
2019年,陈建平创作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组印成功入选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同年,陈建平成功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湘西州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通过篆刻作品加入中书协的会员。
四
聊了许久,不觉天色已晚。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开始踱步赏印。他的陈列架上全放着他的篆刻作品,墙上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
我拿起一方印章细细端详,只见其刀法豪放大气、干脆利落,字体古拙而不失新意,布局疏密有度。
印章上的三个字,赫然是:“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