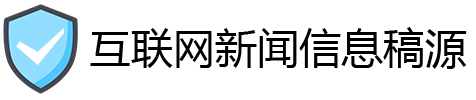粽香 方荣 摄
朱小平
家乡过端午节,麻花炖肉是一道必备的头碗菜。也有鲜菖蒲艾叶挂门楣,驱病避邪;也有白酒里泡雄黄浸蒜瓣,涂抹蚊叮虫咬处止痛痒;只是少见有人包粽子。
虽说咱渔村离屈原投江的汨罗不远,但湖湘文化习俗自古多样,往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渔村自产的糯米,多用于腊月打筛盘大糍粑,有些存记心好的人家,端午还有与粽子同源的糍粑面点,也就省了包粽子。我的裁缝母亲,整日被细密的针线活缠绕,没有空闲。包粽子首先需要采粽叶发糯米,然后添料调味,用麻绳仔细地缠扎,最后架大铁锅上甑笼慢慢蒸煮,工序繁琐。我们都随母亲,偏爱简单便捷的食物。
少时在乡间的所有节日,既是饱餐的美食节,又是我们一家的团圆日。司机父亲从远方买来应节礼品,母亲会早点歇工,给我们换上新衣新鞋,待父亲归来,一齐到邻乡外公家拜节。
颇有些讲究的外公,规定女婿走节不能拖至正节当日。比如正月初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节俗礼仪上讲逢“五”即遇“穷神”和“小人”,去了外公就会“动武”,视作不尊重长辈。当然,这样的事情父亲从未遭遇,他宁可自己省吃俭用,送节礼总要比一般农村人大方体面。端午节别人只送岳父母散装酒小块肉,父亲还要多加一些桃李水果、纸包冰糖及一网丝袋麻花。大姐在路上小声嘀咕:“贫窘的外公,肯定是想就着这些节礼来招待客人。”父母亲同时给了她一个嗔怪的白眼。
次日,我们就在自家过正端午节。厨艺好的父亲,负责做鸡鸭鱼等荤腥,母亲帮忙打下手,她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做麻花炖肉:先把切好的五花肉片,在干锅底煎出油,放一把蒜瓣翻炒,舀一大瓢清水入锅,着少许盐煮沸腾,加麻花炖至松软而不碎糊,撒香葱起锅即成。
父亲做好一桌菜后,总要问我们:“香不香?”母亲做完一钵子麻花炖肉,则有些不自信地问父亲:“熟了么?”
当时我还是个没换牙爱吃软饭的小丫头,会娇嗲嗲地讨好父母:“香又甜!”
麻花炖肉确实很甜。麻花内的糖分,经沸腾的汤水扩散渲染到肉质里,肉也是甜的。父亲咬掉五花肉外层的肥肉,喂我精肉,食罢我咧嘴喊“牙齿挤得不舒服”。父亲即刻放下筷子,帮我掀出牙缝里的肉丝:“满子崽也要吃点不塞牙的肥肉,方可长得乖乖白胖。”
母亲生怕瘦小的我,抢菜不赢,事先夹一个麻花放我碗里。麻花经水煮后,膨松成一根长又宽的丝滑“腰带”。母亲夹得有些费力,端起饭碗靠近菜碗,擎起筷子抬举手臂,将麻花盘卷堆在我的碗里,我吃几截“腰带”便觉饱腹,母亲还叮嘱我把饭吃干净。我假装顺从,端着饭碗下桌游走,趁四下无大人,把饭倒在柴垛边喂别家的小狗,转身悬扣空碗展示给母亲看。我一直没有长成父母希望的白胖模样,天天在村里追猫逐狗,晒得皮肤呈麦麸色,都说我像“油炸鬼”干麻花。
上学后,才知干麻花是用面粉发酵成团,切块儿揉长条,三根组合一起,一抻一拧一并,扭成“8”字形。清代文学家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里这样描述麻花:“渡黄河至王家营,见草棚下挂油炸鬼数枚。制以盐水合面,扭作两股如粗绳,长五六寸,于热油中炸成黄色,味颇佳。”出生河南开封的刘先生说的“长五六寸的麻花”,大概是北方的大麻花。长大后我吃过面上敷了一层蜂蜜、撒了芝麻的天津大麻花,甜得腻人,一人难吃完一个。
渔村方圆几百里未见小麦,只种水稻,自是把面粉看得比米粉稀贵,炒货坊炸麻花总会掺米粉,且最多只小孩手一拃长。麻绳状面粉条在油锅里翻转,由白变浅黄,由黄变金亮,恰如苏轼赞美麻花的《寒具诗》所写:“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刚出锅的麻花,热吃酥脆但易上火;冷却再吃,又干硬硌牙。因此,智慧的家乡人,在端午节独创了这道老少皆宜的松软甜菜——麻花炖肉。
仍记得儿时那些端午节,天井内葡萄架下的圆桌中央,有一瓦钵香喷喷的麻花炖肉。小狗蹲伏桌底,花猫眯起线眼趴窗台,风中尽是栀子花香。桌边主宾位的空椅子,等来了近旁的爷爷奶奶,父母示意我们依序就座,我们一拥而上,动筷开启抢菜……
后来的我,经常这么思忖:假设把“麻花炖肉”的麻花,还原到面粉,把面粉还原到一陇麦田,把麦田还原成一株株需要浇灌栽培的麦苗,我还会觉得麻花炖肉很香很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