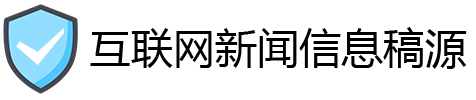徐锋擅长将民间美术的质朴元素与现代创作理念深度融合,在剪纸、刺绣等传统工艺的纹样中提炼抽象美学,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画布上新生。

徐锋作品在古典与先锋的碰撞中实现超越。

徐锋的写生作品则以细腻笔触捕捉生活肌理,让日常场景成为艺术叙事的生动注脚。

徐锋版画《百狮会》底版。他以原始粗犷的笔触与纯粹的色彩张力,对传统民俗进行现代性诠释。
文/ 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吴刚 图/ 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张谨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在“理性崇拜”无处不在的推动下,现代性浪潮裹挟着人工智能呼啸而来,迅猛稀释古老文明的底色、消磨文化基因的记载,在一切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制造无数的不确定性,在人心中模糊了这个世界的样子。而徐锋,一位湘西画家,却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文明本来的灵魂样式进行显影。
在效率和拙质之间,他选择了拙质。
1
徐锋的工作室里,有一卷未完成的巨幅苗画,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摊开。
我从未向徐锋以及相熟的艺术家讨要过作品,感觉跟问人讨钱一样,实在开不了口,卑微的自尊心受不了。但说实话,我对他这幅苗画,真心有些觊觎——因为我是苗族,我能从这幅苗画里,看到了我以为的苗族的样子。
在我看来,这幅画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万物有脸”。画上的花鸟虫鱼,皆有人的面孔,且空间解构、几何扭曲,就像和毕加索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妥妥的“异界风”。
什么,你说苗族是信仰万物有灵的民族——那没事了。
二是“高度抽象”。画面上有故事、有细节,唯独没有场景,每一个局部裁剪下来,都能单独成为一幅作品,特别像是“剪纸”作品。
什么,你说苗画本来就是绣苗绣的底样——那没事了。
瞧,徐锋就这样,粗暴地撕破了那些“文旅叙事”的空间,直达本质和真相,从世俗角度来看,明显没读好“商业互吹”的练达文章,可以直斥为“迂腐”。
2
事实上,徐锋不仅“迂腐”,简直还“木讷”。比如说,你问他有什么“艺术主张”或“价值偏好”,他直接回答你——没有。
他似乎确实没有。因为从认识他起,我见过他太多风格和内涵的作品:一阵子,他沉迷速写,背个画夹穿双解放鞋就离家出走,肉身丈量腊尔山半个月,蓄一圈拉碴大胡子、带几百张速写稿回来,然而往箱子里一扔,出门跟朋友喝酒——按斤算的那种;一阵子,他画和尚,憋在工作室半个月不出门,蓄一圈拉碴大胡子、画几百张只有红黑二色的“平形脑壳”的和尚,然后往箱子里一扔,出门见人,不喝酒,已经戒了;一阵子,他玩连环画,先闭门读书半个月,再花半个月完成几百页高质量插图,出门,将拉碴大胡子剃掉。
不刻意,顺着认知前行,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就描绘表达什么。
也许在他看来,艺术不应是被定义的标签,而应是自由流淌的生命之河,只有摆脱外在框架和复杂价值考量的束缚,才能真正触及文明的内核。
这让我联想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艺术让存在者的存在得以显现”,徐锋正是通过这种“跳脱”的创作方式,让楚巫文化、佛教哲学、原始艺术、现代文化等多元文明元素,在画布上自然融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他的创作过程,是对艺术自主性的坚守,也是对现代艺术功利化、虚无化、同质化倾向的无声反抗。
3
以我一个画界外行的旁观者角度看,徐锋的画,很硬。
他画的湘西傩戏,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狞厉的傩面具,被他解构成存在主义的视觉符码,带给人极度紧致的强烈冲击。
他画的湘西巫事,飘忽的墨线将苗族“魂归祖灵”的生死观,转化为尼采式的“永恒轮回”——亡魂在墨色中跋涉,显影如人类在存在荒原上的集体游荡。
他画的红衣和尚,袈裟邋遢,眉眼孤清,光头如台,红是楚巫的血性显影,黑是禅宗的空性定影,最终在“色即是空”的显影液中,显影出原始崇拜与哲学思辨的双重曝光。
他画的湘西风俗,被其自称为“鬼画桃符”——那些灼目的赭红线条,实为对宁夏贺兰山岩画、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等全球原始艺术的呼应——用跨文明的血色,灼烧消费主义的虚无,显影为对捍卫生命尊严的无声誓词。
他画的湘西速写,更像一本“咒语集”,记录着火塘边的巫歌、雷公山祭的仪轨,存储着即将消逝的灵性密码,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方式,与本雅明笔下的“灵韵”概念不谋而合。
他画的连环画册,徘徊着“意”的幽灵,在《神雕侠侣》《小鳝鱼历险记》《脑筋急转弯》的文本间丝滑地流动。
并非广为人知的是,徐锋在“业余画家”之外还有个“专业教师”的正式职业,他曾将湘西锉花、泥塑、草编等民间艺术引入课堂,曾主持国家级课题“蒲公英行动”,主编《儿童手工实验课程》,参与编写教育部《民间美术》教材,在“国培计划”中主讲《民间美术资源开发》……
4
我觉得,徐锋其实是有价值主张的,或许他就是想以根性表达的方式,在废墟暗影尚未完全笼罩的危险时刻,拾起散落在地的文明瓦片,试图重建某个充满了人性幼稚的圣殿。
现实的悖论在于,他选择用“显影术”还原文化的本真,不过是想将沈从文的诗意、黄永玉的戏谑裂变成更直观的武器,直刺文明危机的核心命题——存在性消解。
所以,当《百狮会》版画中狮鬃卷曲成苗族“窝妥纹”(螺旋宇宙观),他证伪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最地域的符号,在他的笔下蜕变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造影。
所以,当非遗工坊里的孩童用稻草编织“龙鳞纹”时,他蹲身托起歪扭的鸟形编,告诉孩子“稻草沾过土地魂,手暖了它,草就肯讲故事”,将灵性的文明基因,以影子叙事的方式,植入后现代的新宿主体内。
我相信他的坚守,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