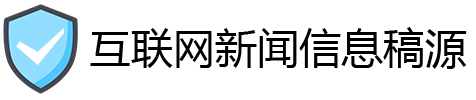芷江抗日受降纪念坊为3门4柱牌坊式建筑,呈“血”字造型,寓意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3500多万同胞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文/ 彭承忠 图/ 彭承双
1
大嘎公,就是大外公,他叫向恒友,坐在我屋后檐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子,爱喝酒,不爱讲话,一句话经常说不顺畅,总是“拼、拼、拼”一通。一开始,以为他说的是“拼了”,久而久之,才知道他说的是“不幸”或“不信”二字,直到我去了芷江,才知这“拼”是“不信”二字的合音bing,又可根据他的表情记为“兵”,他一般用于骂他的儿子孙子时,也用于与人讲道理时或表达不服气时。
他生于1917年8月25日,是老大,有九个小弟,家里穷。他结婚刚个把月,就有消息传来,他家要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去一个人当兵。这是他知道的。在龙山县他沙乡的召市和来凤县百福司的街上,赶场天,当官的早作了抗日动员:日本人不仅打上门来了,还冲进堂屋了,只差把神龛和鼎锅给掂了,这个时候还不奋起抵抗,你是什么人啊、还有什么家啊、还有什么国啊?!——那么得去。“既然去,就我去。”他说,四弟还未成年,老二太猛浪了,老三病魔缠身,都不适合;自己年长会事,遇事沉着,又机智麻利,去才稳当。他的这个想法得到全家人的同意。
于是,他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到二梭乡公所报到,与本乡老砦的同名兄弟向恒友及十多人一起,到了龙山县城。然后,县里派人把他们送到沅陵师管区。
2
师管区是前一个军留下的。在大嘎公他们入住后约一个月,被国民革命军第10军接管了。军长叫李玉堂。大嘎公被分到预备第10师。师长是方先觉。方师长去年底在江西打了一个大胜战,才提拔,是个抗日的大英雄。新兵连训练后,大嘎公被分配到师运输队。第一次为汽车服务,他先是惊讶,后是喜爱,但司机很牛,不让他开,连方向盘都不准他摸。大嘎公反而只是一个卖苦力的,往车上搬东西,主要是搬米,天天搬,上车下车,送到食堂,送到仓库,一身灰不隆咚的,有时也运枪弹衣服。除此之外,就是军事训练,是德国式的那种,比在家里挖土累多了。借物远跳这个项目,大嘎公被军校毕业的朱连长口头表扬过。后来大嘎公也给我爹示范过,就是坪场摆上木匠用的木马(长一丈二尺)三个,从这头跳到那头,中间只能与木马接触一次,我爹也是学了点军操的,却怎么都不合要求,而大嘎公只助跑两小步就向前直飞起来、双手在木马正中一按,就飘过去了,脚稳稳地站在木马的另一头三尺外。大嘎公在这学了一年多,会打各种枪,会装各种弹,还会利用障碍物及死角躲着射击敌人,特别是会拼刺刀和擒拿手。
一九四一年八月,预备第10师接到命令往长沙开拔。这时,大嘎公已是团部文书。在一条小河边往桃源行进时,天黑雨大路溜,他掉下高坎落入水中,等他从洪水里爬上岸来,已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也找不到部队。他一边问一边往沅陵城走,认为到那里可以探到部队的去向。走着走着,他就想回家了,他就改名向至安,说是放簰的龙山人,簰打散了,只有讨米回家去。在官庄,他问路,那人姓向,是家门,他叫他叔叔。叔叔是保长,大嘎公心里踏实了,毕竟都是莲花池向宗彦的后裔。叔叔把他带到乡公所,官庄乡长请他给沅陵常备队(补充队)带封信,到了常备队,那人打开一看,说“欢迎欢迎”。原来信上写着“官庄乡送到壮丁向至安一个”。大嘎公才知自己抵了他们乡一个壮丁的任务,但既来之,则安之,他就这样留了下来。
3
不久,常备队把他送到芷江国民政府防空委员会。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特务旅一团二营七连。他们的营房在东门口、七里桥、竹坪铺、五里牌一带,他住在五里牌。
一到芷江那天,他刚找到自己的铺位,防空警报就呜呜呜地响了,是日本的飞机来轰炸,班长王子唤就把他邀到在一个背角的小防空洞里。不久,就听见当当当的大响,大地随之颤抖。飞机一过去,大嘎公就准备站起来,王班长的手却死死地压住他。王班长说,还有!没想到日本的飞机又掉头飞到头顶上来了,又丢炸弹,当当当地又大响,听到好多木屋垮塌的吱吱声,以及人的呼喊哭叫声。直到警报解除,他们才站起来。王班长说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保卫飞机场和帮助打日军的飞机。
芷江飞机场,是盟军当时在东亚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场合最大时,驻有四个飞行大队、两个汽车中队、两个工厂、两个油弹库、导航台、医院、招待所等十多个团级以上单位,机场外还驻有陆、空、宪总司令部、特务旅三个团和防空部队等十多处军营。空军第一大队住在七里桥、第二大队住在火药港,第四、第五大队住在木油坡,美第十四航空队住在飞机坪,陈纳德的空军司令部设在七里桥,它们都是日军欲轰炸的重要目标。大嘎公他们一集合,王班长就讲了这里怎么重要、大家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死了,也要保住他们活着!
大嘎公有去年的训练打底,领会得快,人又会看事,连长排长班长非常喜欢他,经常让他任小组头目,去侦察敌特情况,执行特别任务。日军要炸飞机场,得先掌握飞机、弹药、总部等要害的位置,就得派人潜入收集情报。大嘎公他们要保卫好这些东西这些人,就得与这些特务、汉奸斗智斗勇。王班长说,上前年,有些汉奸和特务混进来,把一些情况发给日军司令部,来了一次大轰炸,损失重。这些混进来的坏家伙虽然被抓了几个,但他们还有,后面还有人混进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捣乱。这吓得大嘎公到了床上也不敢放心睡,本来他为隐瞒去年当兵的事而特别不愿多讲话,记着“谨开口慢出言”的古训,现在他讲话更加慢条斯理,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个结巴。
4
大嘎公说,一开始他是守油弹库,在库边站岗,按证件让人进出,站得久了才被安排在油弹库里外巡逻,能走动比傻站着好受些。一天三班倒,但加班的时候特别多,因为装油装弹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定数。后来他也守过飞机。飞机没飞时是藏在不远的山窝窝里的,当地人称之为“鸡窝(机窝)”,用花花绿绿的布遮盖着,连去飞机边的大路也铺了这个作伪装。大嘎公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守着,不准无关人员靠近。他还擦过飞机上的机枪,帮助修飞机上的炮和补飞机机翼上的伤洞。他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比如见到熟人,喊“嗨”,不同意就摇头说“鲁”,把东西抛过来叫“趴十”,他跟着学英语的是个美国人,叫“思密斯”。他也守过飞行人员住的招待所。
最让他难忘的是帮助打下日本的飞机。那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一个深夜,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日本飞机又来偷袭机场,他们分布在机场周边的山顶上,看到日本特务发出的信号弹,就也发信号弹,加上一些单位和一些老百姓发的信号弹和打的防空炮,一时间天空被照得亮杲杲的,五颜六色,日机来了也懵了,分不清哪个是真的,混乱中不知道弹往哪儿投,投了也炸不到我们的飞机。我们这方早已准备好了,打他一个猛不知,他们想转弯掉头逃跑,已来不及。我们的战果是打炸敌机九架,重伤敌机四架。声声巨响,把大嘎公震动得哭了起来,泄了他这多日的窝囊气。他后来给我说,这是他十五岁之后的第一次大哭,也是他最后一次大哭。在此之前,他们接到任务,做了不少的木飞机、竹飞机,并贴上与飞机相像的纸,远看就是真飞机,与其他单位做的一起摆在飞机坪里,专门让日本的侦察机看见,让芷江城的特务望见,引诱日本飞机来偷袭。
5
在三十一年后,大嘎公在我们生产队是个有力气却不大会农活的人,被安排与我妈她们喂猪,做些劈柴、挑水、背猪草、挑粪、烧灶火之类的事情。在灶门口,他对我说:“你要多吃油炒饭,吃了锭子(拳头)有钵钵大,像铁锤锤,好打日本鬼子!”然后给我一个用芦茅杆织的绿白色飞机,我特别喜欢它。他让我玩一会儿后,又把它呜呜地飞了几下,然后放在灶边砍猪草的木板上,捡了火炽子射它,同时叫我用我爹给我做的玩具水枪向他射水。当时,我看到他一身湿一脑壳的水,我笑得不行,他也笑得合不拢嘴,却被一个嘎婆责怪“你又找事啰”,才收了笑容,恢复结巴状态。
又十二年后的深秋,我在怀化读书,去了一次芷江,看了抗日受降纪念坊旧址,只有一些圆沙石紧紧地嵌在硬泥中,有些许贴地小草,介绍的人说,将在这里重建这个坊,正征集坊柱上何应钦写的对联,其他的都已得,只差他一个人的,说:谁能记得,奖励一万元。我寒假去大嘎公屋里问,他说,他记不得那对联了。只问晓得七里桥在哪不?我一脸茫然,说,不清楚。他充满期待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我走时,他又问了一句,飞机坪上长了蒿子没?我想,那不可能长蒿子,说,没有,只有一些癞子一样的地草。他黯然神伤地说了一个“哦”。
前不久,我因工作关系,看到有关他的几份档案资料,我才联想到他的那次问话应该别有深意。我也想起他给我讲的那些碎片故事原来是这么完整这么壮丽,我也才发现他是一个被埋没的抗日英雄。于是我决定,要全面了解他。我找听过他讲往事的人回忆,重点走访87岁的大叔彭大国和92岁的八嘎公向恒仁,再不去问,可能大嘎公在乡亲心中就只是个被迫从军、吃了八年兵粮、混于旧军队的一般小兵了。
6
经过那次大哭之后,大嘎公表现得更好,第二年就提拔为排长,此时王子唤任连长、任达煌是营长,黄安佑当团长。芷江保卫战,是大嘎公一生里最忙最高兴的时光。据《芷江县志》记载,43天内,仅第五大队就出动战斗机2500架次,最紧张时,一天曾出动250架次,投放炸弹100多万磅,发射机枪弹80多万发,歼敌约1万多人。这些天里,大嘎公在风中,在雨里,在日下,在地上,在白天,在黑夜,不是运炮弹,就是在加油,不是补轮胎,就是抓特务,不是搬面粉,就是送机梯,经常伴星月陪朝阳,夜晚接着白昼干,白昼接着夜晚干,一天三餐几乎只能吃一半,有几次尿都没有来得及屙,打脱在裤裆里,与汗水混在一起,还是红色的;脸是花的,眼是红的,手是破的,血滴到飞机坪上是黑的,他在白天一直在喊“兵兵兵”,在梦里一直也喊“拼拼拼”……可当听到又炸了多少敌人、打了多少敌机,他又是多么地高兴。可惜大嘎公还是讲得不多,讲了我们也记得不太清。八嘎公们问他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他在做什么,他说:在找椅子,为“芷江受降”作准备。受降官应该在大椅子上坐得雄雄的,这是团长的命令。这一盛况,就是一年后他到汉口训练孝感的新兵时,仍在津津有味地讲。在这特殊的时刻,他是可以口若悬河的。
7
后来,他看到局势不稳,就请假回龙山老家看一看。回老家后,他被逼跟着同名兄弟向恒友等一些啸聚山林的“横强客”跑了两年。
新中国成立后,大嘎公迎来了新生。后来,他还成了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带领社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家乡面貌。
1989年,大嘎公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