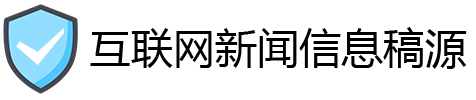任美璇
天青色漫过沅江的晨雾,万寿宫的飞檐挑着微凉水汽,青瓦缝里的青苔漫出墨绿纹路,瓦当垂落的水珠砸在阶前青石板上,溅出细碎坑洼,一圈圈涟漪散开,恰如“天青色等烟雨”的宿命邀约——浦市的雨晨总在等雨,等雨润透石灰岩的肌理,唤醒古穴居人的密语;等雨打湿戏文,让油墨香混着潮气弥漫;更等雨载着辰河高腔的余韵,在街巷间缠缠绕绕。而我,在这酿着万千情愫的雨里等你,等你踏碎烟雨,赴一场跨越时光、非遗传承与深闺心事的千年之约。
雨丝终于斜斜落下,织成一张轻柔的帘幕,打在吉家祠堂雕花窗棂上,噼啪声清脆悦耳。万寿宫戏台上,传来婉转苍凉的辰河高腔——是传承人陈宏满和尚文敏正演绎非遗之魂。陈宏满唱腔苍劲,字字带着穿透岁月的力道,从胸腔迸发,撞在戏台木梁上,又反弹回湿漉漉的空气里;尚文敏嗓音婉转缠绵,如泣如诉,像沅江流水漫过青石板路,渗进老墙砖缝,成了古镇最柔也最深沉的序曲。青石板被雨润得发亮,每道褶皱里都藏着非遗故事,裹着深闺未说尽的期盼。
吉家大院八字门虚掩,像欲说还休的唇。推开时,吱呀声惊醒了在旁休憩的飞鸟。指尖抚过门楣“五福捧寿”的阳刻,触到的不是木头,是时光浸出的包浆,藏着岁岁年年的等待。抬眼是天井裁出的一方天色,像浸了水的素帛,木梁纹路裹着陈年潮意,老窗棂花格里漏进些微凉的风,悬着的红灯笼轻轻晃。等烟雨落满天井就好,雨丝顺着檐角淌下,打湿木桩纹路,让木头沉香漫出来,混着灯笼的红、窗格的暗纹,在方寸天地里织成软绵的网,把时光都裹得温软。
万寿宫铜门环上,绿锈如苔。“门环惹铜绿”的意趣在此鲜活。指尖刚触到冰凉铜面,里头辰河高腔便撞了出来,陈师傅和尚师傅正在戏台上沉醉,入了心的又何止他们。雨滴顺着飞檐滴落,在青石板上碎成无数片小小的天青。这铜绿何尝不是等出来的——等过无数个雨季,等过无数双推开门的手,才浸出这般温润模样,藏着古镇不慌不忙的时光。
傩面具作坊飘着檀香。传承人的刻刀在朱雀眉眼间游走,墙上挂着的傩面具似笑非笑,各藏神通。似乎每个面具都在等三样事:等一场庄重仪式,等一个懂它的眼神,等戴它的人卸下面具时,露出藏在神性下的人间真容。“就像跳傩舞”,他拿起龙王面具,指腹蹭过刻痕,“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我们等的,不过是神性与人性撞个满怀的刹那。”
中元节的沅水格外沉静,断崖下道士的铃铎声惊醒了沉睡的灵魂。纸船明烛顺流而下,载着对外殇者的超度,摇摇晃晃漂向远方,度的是亡魂,也是世间无尽的等待。雨更密了,江面升起薄雾,无数船灯在雾里漂浮,恍若彼岸花开。这一刻,等待有了形状:是顺流的光点,是风里的呢喃,是雨水浇不灭的祈愿,在烟雨里轻轻漾。
门楣上“青莲世第”的题字,被雨水洗得清透,像李家奉了几世的清白。这清白也浸在闺房的窗纸上:素诗笺抄着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墨痕淡了半截,停在“春风拂槛”的“拂”字,仿佛提笔的人听见院外脚步声,攥着笔便停了,等成案头凉透的莲心茶。曾替这青莲世第里的她可惜:困在雕花窗里数青苔,把心事缠进绣线,连春风都要从门楣青莲纹里挤进来——多寂寞,多局促。可又忽然惊觉:我们眼里的“囚笼”,是她一生的方圆天地,庇护她,给予温暖,将细碎时光磨成镜里莲影、笺上墨香,把等待酿成苔衣那样软的安稳。每个时代的活法,本就没有“该”如何,她守着这院青莲的清白,便已是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诗。
比起宏大建筑,更偏爱藏在角落的生机绿意。李家大宅院里有口石头井,初见易被满覆的杂草青苔迷惑,误作沉寂的历史遗物。细瞧才知,井身藏着好看纹路,且非水泥石块砌筑,是嵌了沉船木——在江底泡了百年的“水骨头”,木质浸得如海绵,吸满江潮、攒足耐湿性子。如今嵌在井沿,是顺了它的脾性:苔藓裹住石缝锁着润意,续上江底旧湿;浅浅井水贴着木面,护它不失骨子里的潮;周遭遮天草木,是替它挡去燥风的伞。那些江水泡暗的木纹里,还嵌着当年船舶旧痕,如今裹在苔藓水汽中,恰似把沅江的浪封在这方井沿绿意里,既没失了沉船的魂,又护着它不被干风啃得朽了形。
雨不知何时停了,万寿宫灯火次第亮起,映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恍若撒了一地星子,辰河高腔仍在夜色里飘荡,余韵绕梁。忽懂“三惹”从非偶然:门环惹铜绿,因它始终守在门前;芭蕉惹骤雨,因它永远立在帘外;浦市惹了我,因它在这里等过无数雨季,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坚定。
若浦市的雨还在下,定是下在等雨的青瓦上,下在等风的芭蕉上,下在所有等待相遇的灵魂上,岁岁年年,不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