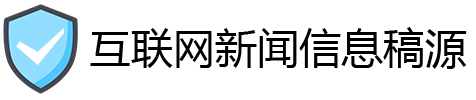潕溪书院内有百年老藤。“藤翁”二字由黄永玉题写。 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石健 摄
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吴刚
1
不怕人笑话,我其实挺自卑的。
也许是由于小时候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缘故,也许是出于生长在湘西“小地方”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地域或民族普遍心理都比较敏感的缘故,长期以来,我从未觉得,在我的身上以及在我的身边,有何可以牛皮哄哄的理由。
少年时,我曾经暗自羡慕那些有条件玩航模、听音乐会、骑单车上学的大城市同龄人;青年时,我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外地风潮学下围棋、跳霹雳舞、写朦胧诗、唱粤语歌——不吹牛,1995年以前发行的粤语歌,我至少会唱95%。
我不知道,在我的湘西家乡,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过于强烈的地域“自豪感”。
年轻漂泊外乡时,有人嘲笑我是湘西土匪,我把他“捶”了一餐;有人问我吃不吃生肉,我把他“捶”了一餐;还有个湘西老乡对外谎称他是怀化人,知道我是吉首人后,又来套近乎跟我讲他是隔壁县的,我同样把他“捶”了一餐……
不可碰触的深刻自卑。
2
我的自卑,还真不光因为物质条件,主要还是文化上的。
我虽然非常喜欢我的家乡峒河峡谷:两岸悬崖兀兀,崖下深林莽莽,林下烟村袅袅,村外稻浪田田,田边河水澹澹,河畔筒车悠悠,有蓝天,有白云,有鸡鸭蝉嘶叫,有鹭鸶飞过……我觉得很美,但是对比挂历里的大城市,长街繁荣、大厦林立、名楼显赫、学府庄严、衣装时尚,那股“我家乡也很牛”的忐忑的膨胀感,瞬间漏气。甚至,当年那种男的坐在草地上弹吉他、女的摆Pose的挂历画,都让我觉得,那是比我高级的、有文化的生活。
即便在狭义文化的领域——我很努力地去学习那些我自认为“很有文化”的雅事,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人玩”的困境——我的周围,没人和我谈格律诗的平仄拗救,没人和我谈柏拉图的国家试验,没人和我谈《金枝》的巫术原理,更没有人和我谈王东岳的“递弱代偿”……倘若我硬要在朋友们“炸口水”的时候强行插入此类话题,必然收获“酸不溜秋”的中肯评价,止增笑耳。
以至于我常常在想,也许我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在“文化不自信”上躺平摆烂,反而能获得“我没文化我怕谁”的另类优越感,再去嘲笑他人。
3
但后来,后来,后来……随着信息扁平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对外界、对湘西的认知日深,随着文化比较变得更加容易,我觉得我又行了——哦不,我的湘西又行了。
我的湘西,是地球演变史的重要记录地,两颗“金钉子”(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漫山遍野的三叶虫化石,见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壮阔奇迹;我的湘西,是第四纪冰川中的绿色气孔,荒野里肆意生长的杜仲、水杉、珙桐、猕猴桃,炫耀着孑遗物种藏身生命避难所的绝世好运;我的湘西,矮寨大桥一带,是全球峡谷最密集的地区,没有之一。
三万九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就在湘西的药王洞里点燃篝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夜晚;四千八百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就在湘西的沅水岸边砌土为窑,烧制了一件又一件精美的陶罐。
在我的湘西,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隐藏着史前大洪水的明确记忆;在我的湘西,讲述着盘弧辛女教化山民的故事,旁证了三皇五帝不遗余力传播文明。
后来,屈原来到我的湘西,对天哭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后来,秦人来到我的湘西,把乘法口诀表,埋进了里耶古井;后来,王阳明来到我的湘西,开坛授课,知行合一。
后来,王阳明的学生吴鹤,在吉首的峒河边,创办了一座“潕溪书院”,至今已传承了512年。
原来,五百年前,我们的湘西,就有了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一样的正经书院,有人像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穿古装摇头晃脑读书的那种真正的古代书院。
原来,我的湘西,祖上很“阔”。
4
更不用说,我的湘西,生活着浪漫坚韧的土家族和苗族,他们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全部具有中华文明意境含蓄、意向飞扬的典型审美。
我的湘西,以异质的自然风光和异质的民族风情著称于世,拥有1座世界地质公园、2个国家5A级景区,还拥有1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达278项的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神秘湘西”天下驰名。
试问,世界上,又有几个地方,敢号称“神秘”却又无人反驳?
凭的就是我们拥有足够独特、足够多元、足够精彩的文化家底。
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融合、发展的全过程,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总特征。
凭的就是我们的文化,凝聚了各族人民共同交往生活的记忆、感知与期许,紧密地筑成了认可认同、相依相存、共信共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凭这一手沉甸甸的文化,我们湘西,该不该自豪,该不该自信?
4月10日,人间春好,“湘西州政协文史教育基地”在潕溪书院挂牌;同日,“湘西文史讲堂”在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大礼堂首场开讲,题目是《诗篇还为故人留——王阳明与永顺土司渊源及影响》,座无虚席。
一缕致力于唤醒湘西文化自信的劲风,于斯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