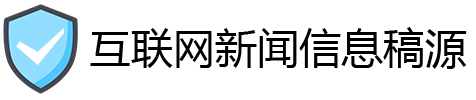陈清峻
沅水奔腾不息,在浦市下湾遗址的礁石上碎成浪花朵朵。欧阳文章溯流而上,在《湘西足履》这部散文集里不经意地触摸到屈子行吟江畔的飘飘衣袂和沉郁顿挫的楚地高歌——这绝非简单的行走,而是以足尖为犁铧,在湘西悠远神秘的时空里深耕,把每一行脚印压成土家苗歌悠扬的韵脚。
有人行色匆匆只为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他的行走却是“与风景相遇、与文化碰撞”。那些沉默在岁月淤沙里的辰河高腔、出土于酉水两岸的石器石斧、流传自古苗河岸边的蚩尤传说……都成了笔下的鲜明物象。在《寻找苗疆边墙》里,他手触风化斑驳的墙砖,没有停留于边墙坍塌、遗迹消失的空泛抒情,而是对持续140多年的“苗防屯政”制度进行理性反思——这一始于清代的制度,通过军事化管理试图“教化”苗民,却也成为民族逐步融合的缩影。在解密《舒家塘的密码》时,他俯身打开蜡黄残损的线装族谱,窥见杨家将后人在此屯边戍守、私塾教化的文治武功。这不仅是散文的书写,更是融文思史笔于一炉的民俗报告、纪实编年,让湘西褪色的往事和那些封存已久的文化密码重见天日、焕发光彩。
从文学的虚构转向历史的真实,湘西的每一寸土地都埋藏着更深回响。在乾州古城巍然的城楼里,炮台上的硝烟已飘散,只剩细雨敲打石阶的寂寥,宛如百年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卸甲归来的叹息声。黄丝桥的落日淌过残垣时,他看见的不只是渭阳县衙旧址的大唐余晖,还有湘西王陈渠珍为百万苍生免于战火的人生抉择。沱江的溪水流过听涛山,他数着波纹里荡漾的,是楚辞的平仄,是虎耳草的芬芳,是沈从文遗落在吊脚楼下的华章。最动人的不是他写出了湘西的魂,而是这魂与魄,竟在笔墨间氤氲出经年不散的白雾山岚。就像那篇《白云深处有李家》,世事沧桑、时光漫漶,他偏要从中辨认出李家寨世代迁徙的踪迹,还有赶圩场上民族融合的喧闹景象,四月初八男女对唱的情歌悠扬,这些场景的再现,充满想象力,让历史变得无比鲜活而灵动,这正是欧阳文章散文写作的独特之处。
文到深处情更浓。读欧阳文章的散文,总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情,触及到人性深处的温暖。他三次探访边城茶峒,在《三进茶峒 三悟<边城>》这篇散文里,他追寻翠翠“永远的凝眸”,最终从“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故事结局中领悟到:不管是沈从文,或者翠翠,其实我们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曾等待过美好的爱情,尽管这些等待有着西西弗斯式的无望或等待戈多般的荒诞,但宿命往往因为无言、无望、无奈而生发一种感伤之美,怀着“凄楚与爱”的深情。《登太平山记》里那位无名的僧人,尽管自己也处于生活的底层,却耗费精力和财富重修庙宇,怀着怎样一种济世的情怀。《老屋》里,高祖父、爷爷、奶奶、父亲一家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互扶持,困难中充满着温暖的人性慰藉。《遥远的距离——从沈从文故居到沈从文墓地》里,大文豪沈从文赤子其人的生命本色以及大艺术家黄永玉顽童幽默的天真,都感人至深。欧阳文章笔下的这些湘西人物,无论市井的小人物,还是闪耀着光芒的大人物,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触动人心。
最有价值的书写往往是对民族精神的洞察、对人文意蕴的体悟。那些被冠以“古镇”“村庄”的篇章,实则是对传统的深情回眸。无论是芙蓉镇联通南北的千年码头,还是岩排溪层层叠叠的梯田稻香,或是桃红李白、炊烟袅袅的水墨中黄,抑或夯吉苗寨里新居落成的上梁歌、抢糍粑,都是充满民族记忆和内在精神的鲜活的文化域场。《湘西的酒文化》中伴随“逮”的一声大喝,陶土碗重重碰撞,让我们见证《血色湘西》的豪气干云。《筸军的背影》中“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的追述,让精忠豪义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不错,这就是湘西,并非被外界误解的只有赶尸、放蛊、土匪的“妖魔化”湘西,而是血性柔情并存、历史人文荟萃的“这一个”湘西,这种“同情之理解”让欧阳文章这个异乡人也找到了他灵魂的原乡。同时,我们也忽然懂得——所谓文化寻根,不是博物馆里干瘪的标本复原、不是猎奇的展品摆拍,而是让古树断茬萌发生机嫩芽。
二十余载春秋,欧阳文章徜徉于湘西的山山水水,屐痕到处生烟景,泼墨挥毫化绮霞。沅水听涛时,江水将屈子的离骚、王昌龄的冰心、沈从文的橹声、金庸的侠情都糅进文章段落;武陵问道处,雾霭把坍圮的城墙、梯田的曲线、银饰的寒光都刻入诗意骨节。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事物,被他的文字召唤或点燃,让每个读到《日暮亭子关》《最后的卫兵》这类文字的读者,内心深处都会被这些执着坚守一方的戍卒后裔所深深震撼。
合上书卷,封面上“湘西足履”四个字仿佛有了温度。这不是终结,而是某个时辰的再出发——在湘西的某个角落,那个倾听高山川河、触摸古镇村庄、体察人世风物的身影,永远在跋涉,永远在书写。正如他在后记所写:“生命不息、行走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