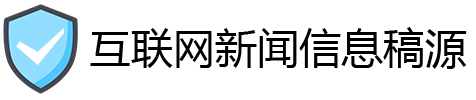渡过江,去见江东寺。
文/图 周昕
十月十五,雨歇天青。秋意像浸了凉水的棉絮,轻拢着孝坪镇的轮廓,风里漫着桂香——是刚揉碎的糖霜般的甜,沾在衣角便不肯走。我与文友揣着满心雀跃,叩响了浦市对面江东村的晨扉。这片在梦境里绕了千百回的灵秀地,正以晨露未干的枝丫为簪,别着几枚初染鹅黄的叶;雾纱是晨露织就的帘,风一吹就裹着湿意漫过来,轻轻漫过鞋面,像少女半掩的笑靥。
一
江东的山水间,像藏着三卷未曾合拢的千年古籍,纸页间漫着时光的沉香。浦口宋城遗址是开篇那页泛黄的宣纸,北宋元祐年间的墨痕,经了千百年风雨磨洗,依旧倔强地凝在砖砾上——不是模糊的淡,是深嵌在岁月里的执拗。八座码头错落在五十万平方米的遗址上,像串被沅水潮气泡软的珍珠,散得随性,却藏着古渡的旧韵。
岸边芦苇已抽了白絮,风过处便簌簌扑向青灰砖砾,落得轻软,像给千年遗址撒了把揉碎的雪;砖缝里嵌着的细碎蚌壳,是沅水这位史官刻下的标点,壳上还留着江水漫过的浅痕,默默记着宋元的潮起、明清的潮落。
通判署衙的墙基,犹如一段被悠悠岁月啃啮的古老竹简,尽管只剩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却仍能从斑驳榫卯间,窥得古人藏在木纹里的智慧——那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技艺传承。墙根处的野菊开得泼泼洒洒,细碎的金黄缀在断壁的褶皱里,为这份沧桑添了几分秋的鲜活。这处曾能直奏天听的副官治所,原是古代集权制度里一枚精巧的活扣,把江东的山水形胜与官制肌理缝得严丝合缝,恰是天作之合。
回溯至1996年,那场汹涌的洪水,像天地间挥毫的画师,泼墨间让八大码头遗址从浊浪里显了形。红砂岩石砌就的台阶,恰似一排排泡在光阴里的琴键,每一级都载着历史的沉,台阶缝里还嵌着几片被秋阳晒枯的枫叶。八家巷子的砖石勾缝,细若游丝,却牢牢锁着千年不散的商音。指尖拂过江水浸软的石面,木纹般蜿蜒的水痕里,像浮着黔地矿产的清泠,又裹着荆楚风物的温,恍惚间能看见满载货物的竹筏从历史深处漂来,欸乃桨声碎在石阶上,溅起点点星子——那是过往与当下撞出的光。
江边冶铁遗址,该是这三卷古籍里最炽热的篇章。战国矿渣里的碳十四数据,像把烫热的钥匙,悄悄打开了千年炉火的密码。沅水到了这里,像化作一座烧得通红的巨型熔炉,把从清水江远道运来的铁矿石,锻造成能犁开土地的铧,让山地的硬与平原的软,在烈烈火舌里融成了一处。江风裹着秋凉掠过,卷起地上的炉灰——连土层下埋着的那些,过了千年,还沾着淬火时的丝丝余温。侧耳听,仿佛能听见铁汁坠地的瞬间,与江水撞出的滋滋回响。
这条“水上丝绸之路”的古航道,早把群山的呼吸与江河的脉搏,锻成了一枚不生锈的纽带。沿江的八大码头间,还散着堆堆铁炉渣,像沉默的守望者;炉渣旁的狗尾巴草染了浅褐,在风里轻轻晃,似在诉说往昔的辉煌。在那个《盐铁论》见证王朝更迭的时代,这片土地藏着的秘密,还等着人们一一揭开。
二
江东寺静卧在沅江东岸,像尊慈悲的侧卧罗汉,满身披着秋阳的柔光。寺外的古银杏正漫出浅黄,零星叶片飘下来,铺在寺前石板路上,像撒了层揉亮的碎金。寺宇的红墙在粼粼波光与秋阳里,渐渐褪了艳色,像件浸过岁月的旧袈裟,泛着古朴的沉。
大雄宝殿内,四根金丝楠木殿柱,像四位立了千年的巨人,稳稳撑起云絮般轻软的飞檐。檐角悬着的铜铃,被带秋意的风轻轻拂过,悠悠晃着,抖落一串空灵的佛号——那声音似穿越时空,直抵人心深处。释迦牟尼佛像的衣褶里,积着时光沉下的香灰,是信徒虔诚的印;十八罗汉的眉峰间,像还凝着宋元清晨的露,透着历经岁月的静。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处直径五米的地坑。从前的“自动转轮藏”就在这里转,一圈圈转着,画下数百年岁月的年轮。经卷随轮旋转时的隆隆声,早渗进了楠木的纹理,与沅水的涛声和着鸣,在空殿里漾起层层涟漪,说着古老的佛缘。
寺院的篆书门联“有福方登三宝地,无缘难入大乘门”,刻得深透,每一笔画里,都嵌着历代香客的虔诚目光。门联旁的桂花树缀满花苞,风一吹,淡香就漫进殿内,与香火的味缠在一处。
大雄宝殿内,如来佛祖塑像两旁的木柱上,挂着副传了千年的对联:“木鱼敲坠天边月觉觉觉觉先觉觉后觉总是觉觉,金钟撞破岭头云空空空空色空空相空无非空空。”这联是神来之笔,把佛教的深与中国文化的厚,糅得恰到好处。
我站在联前许久,任禅意漫进心里。上联“木鱼敲坠天边月”,寥寥数字就勾出静远的夜:深秋的夜,木鱼声破了寂,像把天边的月轻轻敲落。“觉觉觉觉”叠着,既像木鱼的脆响,又藏着佛门“觉醒”的意;“先觉觉后觉”是说,无论早醒晚醒,终要抵到觉悟的境。
下联“金钟撞破岭头云”,绘的是雄浑的景:洪亮的钟声穿了秋雾,撞破岭头的云。“空空空空”叠着,是金钟的沉响,也是“空”的禅理;“色空空相空”,正是对“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浅说,外在的“色”与内在的“空”,原是缠在一处的。
再看用词,“木鱼敲坠天边月”与“金钟撞破岭头云”,既绘了秋日的美,又裹着诗意与禅意,让人见了景,心也跟着静。“觉觉觉觉”与“空空空空”两组叠词,让对联读着有韵,像首轻吟的歌。这联像位智者,劝人借木鱼、金钟悟禅,更要惜眼前的秋、心里的静,别在尘世里迷了自己。
想着,便念起沈从文先生。他当年在此停留时,大抵也对着这联沉思过吧?以他对文化的敏锐,定能懂这联里的禅与悟。先生对辰溪的情极深,九十多年前就赞这里“任何时节,都是令人神往的美丽地方”。他曾特意住进江东寺,在这片净地里写下《箱子岩》的初稿,文中说:“那座大庙,景致之美,竟超过北京的碧云寺……庙中古松参天,要五人合抱;老梅树高三丈,开花时像一树绛雪。”那时先生尚年轻,投笔从戎,在寺里住了二十多日,还提过殿里藏着“大藏”,像座五丈高的塔,雕满了菩萨,壮观得很。
江东寺的“大藏”早成了辰溪的文化名片,引着人来寻。先生还曾细写转轮藏:“寺侧院立着座转轮藏,木头做的,高三四丈,上下用斗大铁轴接着。三五人扶着雕龙的木把手转,声音像龙鸣,凄厉又绵长。说是仿龙声做的,半夜转时,十里外都听得见。本地传,天下共三个半转轮藏,浦市占一个。”读着这段,像真见了转轮藏转起来的模样,听见了那声龙鸣。
姚家祠堂的青砖黛瓦,像本无言的书,写着另一种“经文”。祠堂外的枫树红透了,叶片落在黛瓦上,像给屋顶绣了层红绒纹。檐角双龙戏珠的浮雕,经了岁月磨,像凝成了琥珀,活灵活现。“祖德仁爱天地鉴”的族联,浸着百年桐油的厚,是家族传下来的绳;八字祖训刻在墙上,笔画间长着嫩绿的苔藓,像岁月盖的印。
乾隆年间的功德碑,像位端坐的老者,碑文被风雨磨得发亮,倒更显庄重。碑前的石台上,摆着村民刚采的野菊,添了丝秋的活。四川宗亲送的鎏金长联“祠枕东山大气磅礴三公会聚鸿基固,门迎沅水巨流瀚漫一宗同源世泽长”,把宗族的根与山水的脉拧成了一股绳。梁柱间飘着桐油的香,混着秋日草木的气,六个世纪的家族记忆,像坛陈酒,在岁月里慢慢醇,说着代代相传的故事。
三
大半日的探访,像踩进了时光的裂缝。宋城的砖上,沾着宋元的雨、秋日的草,指尖一碰,是千年的温;码头的石上,浸着明清的水、枫的红,足尖一踏,是岁月的褶;寺院的木里,藏着唐宋的佛音、银杏的影,耳畔一听,是信仰的轻;祠堂的匾上,凝着明清的族训、玉米的香,眼底一看,是传承的重。这些文化的基因,正以新的模样在现世扎根——老墙下的秋花、檐角的炊烟,都是它们抽芽的样子。
姚家祠堂外,孩童的笑声惊飞槐叶,叶片打着旋落在青石板上,和老人们剥板栗的沙沙声叠在一处。家常话像溪水似的漫过石路,“父慈子孝”的祖训,化作檐角的秋风,轻轻拂着晾晒的衣裳——衣裳上沾着秋阳的暖,像先辈的手,轻轻拢着寻常的日子。
“和美乡村”的建设者们,踩着先人走过的石板路,脚步与沅水的涛声同频。他们把历史的厚重,酿成往前走的底气,在传承里织着新韵:古寺旁的新楼、遗址边的步道,都在说“旧韵新声”的故事。
暮色渐浓,秋阳给江岸镀了层金边,芦苇荡在暮色里泛着白,晚风掀起层层浪。古寺飞檐和新楼轮廓,在霞光里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握手,砖的古、木的老、楼的新,在秋光里融成一幅画,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当下。
秋风又起,最后几片银杏叶落进沅水,不是凋零,是把宋城的砖屑、古寺的香灰、祠堂的桐油香,都裹进浪头里。浪头翻涌时,每一朵都载着千年文脉,往新时代的岁月里流。
沅水还在滔滔流,水面映着霞光,比从前更清、更亮。因为每一朵浪花里,都藏着历史的回甘、秋日的温柔,藏着江东人把岁月酿成诗的力量——这力量,正推着时光,往更盛的秋、更暖的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