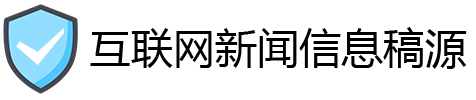团结报全媒体记者 吴刚
1
我家有一口圆底铁锅,黑黢黢的,像一扇反攻颜值的盾牌。我妈说,这锅年纪比她还大,见证过清贫岁月里的锅贴老苞谷粑,也伺候过这些年我尝试的香煎金鲳、酱卤牛腱,以及我女儿捯饬的什么黑椒牛柳、番茄意面。无论食材土气还是洋气,在这口锅里一番颠簸,总莫名带上一股“家味”。
对这口锅,用归用,却从来都毫无感觉。后来读了些杂书,走了些地方,才惊觉这口圆底铁锅,几乎是所有中国厨房的“统一制式”:从东北的灶台到岭南的排档,灶火舔舐的,多是这相似的弧形。我突然意识到——事情,很可能不再简单了,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沉默而坚定的文明抉择。
这抉择,很可能导致了东方餐饮文化踏出一条偶然的、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精彩大道——“中国菜”于斯肇始。
有趣的是,最初的动因,并不是为了“登顶味觉巅峰”,反而更像是被日子逼到墙角后,摸到的最趁手的那块砖。
2
这首先是东亚大陆铁资源匮乏造成的。春秋以来,“盐铁专卖”已成制度——铁作为战略物资,得先紧着刀剑和犁铧——前者保江山,后者活人命。至于炊具的丰富样式,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民以食为天”面前,乖乖让路吧——华夏没有多余的铁,去给煎牛排、烤面包、炖浓汤各自打造一套专属器皿。
于是,一口“万能锅”成了最优解。圆底,能聚火;深弧,便翻炒;铁质,传热快。炒、炸、熘、煮,它都能比划两下。这是“物资的稀缺”逼出的“工具的收敛”。就像湘西山民的柴刀,能砍树、能开路、能防身——所谓“一专多能”,往往是“无路可走后的飞升”。
3
然而,光有这口“万能锅”还不够。锅是死的,人是活的,还得听从一个更强大的“指挥官”——中国人肚子的“绝对命令”。
华夏中原可能是农耕最彻底的地区,长期的饮食结构以谷物为主,使得菜肴的核心功能在于激发主食的食欲。因此中国菜的第一任务,不是愉悦舌尖,而是“下饭”。
中国饮食习惯,在此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分野——食物(foods)被分成“饭”和“菜”(大多数老外饭即是菜菜即是饭)。
记得小时候,家里偶尔有好菜,小孩子多伸筷子,都要被大人用筷子严肃撩开。于是从小就觉得,空口吃菜,罪莫大焉。
既然是“为了下饭”,那么清蒸水煮,滋味寡淡,火上烘烤,速度太慢。唯有“炒”——铁锅,旺火,热油,食材下去,“刺啦”一声,“锅气”升腾,菜香扑鼻而来,幸福感满满。
你要是炒碗豆豉辣椒,半条街都弥漫着劲爆“脚丫味”,勾起路人条件反射的口水。哈哈。
看,锅的形,被社会的胃,捏成了必然的模样。
4
历史走到十六世纪,海上来了“不速之客”。辣椒、番茄、土豆、玉米……来自美洲和南洋群岛的食材香料,撞进了中国厨房。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它们跳进那口早已等候千年的圆底铁锅,在猛火热油的催逼下,辣椒的烈,被激发出复合的香;西红柿的酸,转化成果味的鲜。外来的“材”,遇到了本土的“器”,非但不打架,反而如干柴烈火,烧出了一片味觉的新天地。
这就像湘西的腊肉,本是储存食物的无奈之举,却因烟火的熏染,意外获得了穿越时间的醇厚风味。那口铁锅,也从应对匮乏的“无奈之举”,蝶变为创造无限风味的“核心引擎”。“全球化”的馈赠,让这条古老的路径,突然看见了更辽阔的星辰大海。
5
故事的高潮,竟在遥远的法国实验室里被揭晓。二十世纪初,法国化学家美拉德发现,食物最诱人的香味,源于氨基酸与糖在140-165℃下的热烈拥抱。这叫“美拉德反应”。
而中国铁锅,再次意外成为这个反应的“天选之器”:圆底聚热,瞬间可达临界高温;铁壁均匀,让反应畅快淋漓;颠勺翻炒,是厨师手动控制的精准反应时长。所谓玄妙的“锅气”,在科学透镜下,不过是美拉德反应产物的浓郁气溶胶。
你看,这口始于特定条件和务实精神的铁锅,在历史的翻炒中,意外地叩响了美味科学的大门。这哪里是设计好的蓝图?分明是山重水复后,撞见的柳暗花明!
炊烟不息,锅气不断。那缭绕的,是食物的香,是一个文明在应对约束时展现的务实智慧与创造韧性,更是一条于偶然中走出、在必然中璀璨的独特道路所绽放的造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