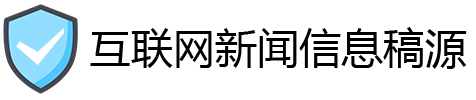水与城共生。

船在水上休憩,听水的絮语。
文/ 杨剑城 图/ 石流
人是离不开水的,这话一点不假。水是从山里来的,从地下冒出来的,从不知道哪里流下来的,弯弯曲曲地往人住的地方去,就成了河。河水养活了人,人也守着河,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日子刻在河边石头上,埋进河床泥巴里头。湘西多山,山和山中间,只要有一点水路,就有村子,有寨子,这沱江就是这些高高低低的山上挤出来的一条血脉,它不大宽广也不汹涌澎湃,就那样静静的,在武陵山脉东边的高原上面,试探着,摸索着,淌了出来,那源头呢,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很小的小点,一条叫乌巢河的大峡谷。那里没有碑文亭台,只有零零碎碎的乱石堆,还有那些缝缝里的清水,清凌凌的,不知疲倦地往外冒。
初生的水是怯懦的。细弱的一条,在深谷阴影里,几乎看不到它在流,只能听到声音,那种极幽微的、仿佛叹息般地响动,贴着石头脊背走,吮吸苔藓的湿气,汇集落叶下的暗流,慢慢地,那线变粗了些,有了些力气,便开始冲刷,带走一些泥沙,在石头上留下浅白的痕。它没有选择方向的余地,山势陡峭往下掉,它也就跟着掉下去。路上又有更急促的水流汇入进来,那些水流或许也有自己的名字,在某个山坳处,被某几户人家唤作“龙塘溪”“麻冲河”,它们来了之后,就不再分彼此,全都成了沱江,水声渐渐厚起来,从叹息变成了絮语,也变得从容起来了。
水流出深山,眼前忽然一敞。山势缓下来了,出现了一片不算开阔却平整得叫人心安的谷地,这就是凤凰。水到这里来,好像也走得慢了些、累了些,想歇一歇脚似的。于是它舒展开身子,河面宽了,水色也由那深山里的墨绿,变成淡淡的青碧。人也就在这时候出现在水边。最先是什么人呢?是逃难来的吧,是屯垦戍边的士兵吧,还是追赶猎物到此,见这里水土好,就再也不愿离开的人呢?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这个地方古称“武陵苗疆”,是“五溪蛮”的地方。那些名字,透着中原看边陲的那种疏远而警惕的目光。但水不管这些事,它只认得生命。人们在河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在岸上垒起了第一块石头。
那石头,是苍黑的。湘西山里多的是这样的石,沉甸甸的,肌理粗粝。人一块块地从山上背下来,从河滩上捡回来。他们不用尺子,不用规矩,只用眼瞄一下,用手掂量一番,大石垫底,小石填缝,一层压着一层,斜斜地垒起来。这墙便有了根,在岸上的泥土里生出来了,下半截终年浸着水汽,长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绒毯般的青苔。墙垒得高了,就有了城的样子。这城,起初怕也只是个土围子,是个寨吧。后来呢,有名字了,叫“镇筸”。这个名号里头带着兵戈之气,明清两代朝廷要经营西南的时候,这里就是咽喉,门户啊。于是乎,戍卒来了,工匠来了,流徙而来的犯官和商贾也来了。这些石头造就的,不只是家园,也是关防。
河水看着这一切,看那些穿号褂的兵丁在晨雾里沿着它去巡逻,沉重的脚步声落在吊脚楼下的水波里。看苗家阿妹背着高高的竹篓,在河边石阶上捶打浸湿的土布,“嘭——嘭——”的声音,很结实也很空阔,把几尾游鱼惊得从下面跃了起来。还看见赶尸的巫师摇着摄魂铃,在漆黑的夜里带领一串沉默的影子匆匆走过它的某一座桥下,那铃声响过之后便再无声息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它们都是河水的记忆里的泥沙,被一层层沉淀到最深的河床底下去。
河上的桥,是人的手臂,伸向对岸。最早大概就是几根木头,颤巍巍的,人走过,影子在水里也颤着。后来,有了正经的石桥。虹桥便是其中之一。三个厚重的青石桥墩,稳稳地坐在河道里,任水流日夜冲刷。桥面是木做的,上面盖了廊起檐,就成了市集,成了茶馆。人在桥上买卖,在桥上歇脚,在桥上看风景,在桥上说闲话。那桥就不再只是路,它成了一种热闹,一种喧哗,成了活在人群里的一个活物。桥洞下,水更幽深些,船从下面过,总是要慢下来。艄公的篙子点下去,触到的是时间的底,绵软而深不见底。
有桥,就有渡口。渡口是路的尽头,也是路的开始。北门外跳岩不算真正的渡,但却是最有趣的涉水之路。几十个石墩一高一低排成两行,在这岸上蹦到那岸去。水浅的时候,大半都露出来,敦敦实实的;水涨起来,就只剩下一个顶了,像是一串黑念珠浮在水上。人走上去要当心些,看准下一步。一步一步地,身子微微晃着,影子也在水里碎开一片晃动的光,这就慢下来了,不能不慢,快一点就会跌下去。于是这跳岩就成了河上的琴键,日日夜夜,被来往的脚步敲出疏疏密密的生活节奏。
船是水的知己。这河里的船,是极瘦长的“乌篷船”,一头一尾尖尖地翘着,像一片剖开的苇叶,它不吃深水,在不深不浅处走最稳当。艄公都是老把式,一手撑篙便定乾坤,那篙子是竹做的,头儿包了铁尖,看上去轻巧,实则沉得很,篙子下水,并不是乱点,只在那些关键地方、力道用尽的时候轻轻一点,船就听话地转了向或者快了一点儿,他们大多沉默,目光落在远处的水面,或者是岸边某一块熟悉的石头上,他们的手关节粗大,布满和水、和竹篙摩擦出来的硬茧,那是张画满了河流纹路的地图。
水也养活生命,不单单是人。河里鱼多得很呢,一种像小指长短的“白条”,一群群在临水的石壁阴影间倏忽来去,银亮的鳞片一闪便不见了影子。还有另一种当地人叫“千年鱼”的家伙,其实是大鲵,在深潭的石缝中藏匿着身子,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发出婴儿啼哭的声音。“草”也是满眼碧森森地在水流缓慢之处轻轻摇曳,像是河水自己长出来的一种绵延不断的思绪吧?夏天到了以后就会有萤火虫从草丛里飞起来,一团团幽幽的光低低地掠过水面,分不清到底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还是水底梦做的泡泡冒上来了。
河与城,就这样长在了一处。吊脚楼的木桩,深深扎进岸边湿漉漉的泥土里,也扎进了河的肌体里,楼的影子,白日时分是短而黑的,压在粼粼水面上;到了黄昏就拉得很长很长,很淡很淡,在一片金红光晕中溶化掉。妇人推开临河的窗,把长长的竹竿支起来,晾刚洗过的衣衫,那些衣衫滴下的水珠儿一串串地落下来,落在河上,漾开极小极小几乎看不见的波纹。炊烟也是从这些木楼上冒出来的,先是一根笔直的线,很快就被河上的风给吹散了,化成片青灰色的雾,淡淡地浮荡着,笼罩在水上,罩住河边石阶和木船。那烟是有味道的,柴火燃烧的味道,混杂着锅灶里的米粥味或者腌菜味,丝丝缕缕飘到河里去,又顺着流水漂向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水是镜子,照着岸上的朝夕。清晨的天像蟹壳青,水面也像蟹壳青,雾气从水面上蒸腾起来,乳白色、流动的,把一切都变得朦胧又柔软。早起汲水的妇人蹲在石阶上,木桶“咚”的一声沉入水底,提上来的时候满满一桶清亮晃动着微明的天光。白日里一切就清晰响亮了起来,洗衣的棒槌声、船工的号子声、游人的谈笑声、店铺伙计的吆喝声都浮在这河面的空气里。 阳光直直地照下来,水就成了千万片碎金子,晃得人睁不开眼。到黄昏的时候,西边的山把落日揽住,泼天的霞彩先是金色后来是橙色再就是酡红色,全沉进了河里头去。河水便醉了,流着一河温热的、化开的光。夜里来了,灯火一点点亮起来。岸上的灯都是暖黄的,一盏一盏映在水上,被水流拉成长长的、颤动的光带,就像一条河自己给自己点亮了一条路似的,在黑漆漆的地方给自己的脚掌挑明了道路。
但是水是恒动的,城却是执拗的静,这相依里便也藏了无尽冲刷与抵抗。雨季到来时,山洪暴发,清浅温柔的沱江,在一夜之间换了脾气,浑黄的水像一头咆哮着从上游卷过来的怪兽,吞没石阶,拍打城墙,水面漂浮断木、草屑,甚至还有不幸的家畜,河水暴涨得几乎要淹到那座虹桥桥面上去,人们躲在家里听着外面骇人的水声,沉默地等待,等它退去,之后就留下一层厚厚的腥味淤泥和满目疮痍。但过不了几天时间,大家又会出来,洗一洗台阶,修一修船,把被洪水冲倒的跳岩石墩一个个扶起来摆回去,河岸石头上便又多了几道新的深深的划痕,这些痕迹记录下水的暴怒,也记录人的韧劲。
水边的生活,是具体的,是琐碎的。生活的污秽,也一并交给河水。洗菜淘米,是它;刷马桶、倒夜香,也是它。不言不语,照单全收。那清澈的水,在城的下游,总是要混浊一阵子,裹挟着人间的种种余沥,向下流去。但它有自净的方法。流过一段,经过几处回湾,几片沙洲,那水便又渐渐地、努力地恢复起那种青碧的颜色来。这是一种沉默的宽容,一种无言的承担。人知道它的澄澈,依赖于它的滋养,于是就把自己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交付在这条绵长的流水里。婴孩出生了,用这河里的水给他洗澡;女子出嫁了,对着这河梳最后一次闺中的头;老人去世了,孝子贤孙们就到河边“买水”,为死者净身,送他干干净净地上路。于是这条河就成了人的一生见证,从始至终。
时间像这水一样,流走很多东西。戍卒的铠甲生锈了,土司的威风没有了,赶尸人的铃声也早没了踪影。石板街上马蹄印被一双双现代鞋底磨得光滑而淡薄。河边码头上,再不会堆满要运到辰州、常德去的桐油、朱砂和药材,那些乌篷船装着更多的四方游客,看风景的人。他们举着相机,对着吊脚楼拍,对着虹桥拍,对着穿苗服摆姿势的姑娘拍。河水还是那么流淌,但映照出的却是另一番世相,岸上有咖啡馆,有酒吧,还有霓虹灯招牌,那光打在水上就是另外一种斑斓,另一种喧嚣。
但是有些东西是水冲不走的,像是那些苍黑的石头城墙,泡了百年,刮了百年,还是立在那里。还有那座虹桥,桥墩上留着一层深一层浅的水痕,那是岁月写下的天书,没人能懂。再有就是跳岩上的脚步声,一代人踩过去,另一代人又踏上来,石墩顶被磨得跟镜子似的,照出人的影子,也照出逝去的时光。到了黄昏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本地老人,在河边的石凳上坐着,对着河水一袋接一袋地抽烟,他们也不说话,只是一直看,看着水,看着船,看着对岸的灯一盏盏亮起来。他们的脸就像岸边的老石头一样,沟壑里藏着太阳落下来时剩下的余温,还有河水上冒出来的水汽,他们是这条河,这座城活着的记忆,他们沉默的样子里面就有水在流淌,也有山在静默。
夜深了,人声、灯火都稀疏下去的时候,河水的声音就清晰起来。那声音是恒久的,低沉的,并不是哗啦,也不是潺潺,而是一种浑厚得包容了一切的“汩——汩——”之声,像大地舒缓的呼吸,又像是一个极老极老的梦呓,它流过城墙根底,流过桥墩缝隙,流过每一根浸在水里的木桩,流过每一块被岁月磨圆的跳岩,带走了日光下所有的浮华和声响,只留下这亘古的节奏,在这个节奏里有乌巢山谷石缝间的沁凉,有苗家女子捣衣时的回响,有戍卒沉重的脚步,有商船遥远的欸乃,有孩子落水时的惊哭,有老人临终前的叹息……所有的一切都被它吸纳进去,调和在一起,化成了自己的流淌,平静的,深不见底的流淌。
我时常在想,这沱江是凤凰的母亲呢还是她的儿女?是一条河养育了一个城呢,还是一座城给一条普通的河流取了名字、历史和魂魄?其实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它们早就已经长成为一体。一座城就是河岸边站立着的一块会呼吸的石头;而一条河则是城池血脉中流淌着的一股不会干涸的血液。人,就在这样石与血之间一代又一代活出了风景。
天边露出第一缕鸭蛋青的曦光,雾气又从水面冒出来了。河水在晨光里是惺忪的、灰白的颜色。早起的船工解开系船的缆绳,“乌篷船”轻轻一荡就滑进主流中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